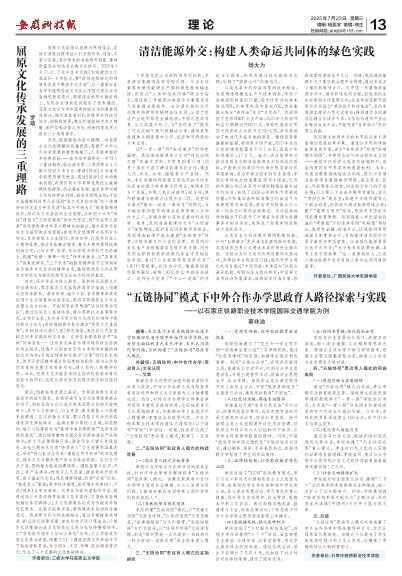发布日期:
清洁能源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绿色实践
文章字数:1766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发展清洁能源则是破局的关键。作为全球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和绿色技术输出国,我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深入开展清洁能源外交重塑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格局。从沙漠戈壁的光伏矩阵到热带雨林的特高压电网,从动力电池产业链到绿色金融创新,中国以技术普惠、合作共赢为核心,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负担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推动世界能源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从“一带一路”到“全球南方”的绿色辐射。我国清洁能源外交是对“绿色丝绸之路”的深化实践,当前我国累计同100多个国家开展了清洁能源项目合作,覆盖光伏、风电、水电、储能等全产业链。例如,中企承建的阿联酋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项目,年供电20万户家庭,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40万吨,使阿联酋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13%。这些项目通过“建设—运营—本地化”的模式,为当地培养出优秀的清洁能源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并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科技创新。此外,我国清洁能源外交与“全球南方”深度绑定,面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我国清洁能源产能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实现资源互补与协同治理。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链需要印尼镍矿的支撑,同时我国也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在中东地区的市场,通过“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等机制,我国为印尼、越南等国提供绿色融资,破解190亿美元/年的资金缺口。这种合作打破了“中心—边缘”的传统分工体系,形成资源与技术的双向依赖,创制了“南南合作”的新范式。
从成本革命到经验共享的技术赋能。我国通过规模化生产与技术创新,降低了全球绿色转型的门槛,将光伏组件的成本降低80%,风电度电成本降低60%,清洁能源正在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我国供应了全球80%的光伏产品,2023年光伏组件的出口额超过2000亿元,帮助巴基斯坦等国光伏发电占比提升至5%-13%,并有效推动了电动汽车在当地的普及。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若排除中国产能,2023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将不足1吉瓦,远低于实际规模的117吉瓦。此外,清洁能源外交推动我国自主的清洁能源技术标准走向国际,中国制定的漂浮光伏设计规范被印尼等国采纳,成为东南亚国家的行业基准;中国分享的电力技术覆盖30多个国家,巴西的美丽山项目在采用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标准后,实现了2000公里的电力零损耗传输;中核集团在阿联酋推出的高温气冷堆模型等创新成果,推动中东核能合作从单一设备出口转向系统集成。这些技术标准的输出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事务中的话语权,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适配成本。
从项目合作到政策协调的机制创新。针对“全球南方”发展清洁能源的融资难题,我国探索出多元化模式来共担绿色金融风险。亚投行为印尼的光伏项目提供风险对冲,并降低中企的投资门槛;埃及苏伊士湾风电项目通过“中国贷款+本地股权”的混合融资机制,实现资金与责任共担;中国碳交易市场与东盟国家、海湾国家逐渐互联,积极探索跨境碳信用互认。同时,我国清洁能源外交注重区域治理平台构建,通过多边主义强化制度性合作。在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推动区域电网互联,促进老挝水电与泰国光伏优势互补;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牵头设立“清洁技术转移基金”,资助非洲国家建设小型光伏电站;推动建立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为信息沟通和产业合作提供对话平台,不断完善“全球南方”的政策工具箱。
我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本质是以技术普惠推动发展权再平衡。通过分享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方案,助力“全球南方”跨越“高碳增长陷阱”,并重构全球气候治理的正义性——减排不应是发达国家的道德特权,而是所有国家平等享有的发展权利。未来,我国仍需警惕地缘政治风险,强化中资清洁能源项目数据的透明度,突出就业、民生、环保等社会效益,回应西方炒作的不实论调;引入第三方企业参股项目建设,淡化“中国主导”的标签;加速产业链共建和人才联合培养,拓展新兴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推广“能源互联网”经验,帮助更多国家实现能源智慧管理。我国将进一步把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标准体系的“软联通”相结合,在绿色金融、标准互认、区域协同等领域深化制度性合作,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正如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所言:“当今世界的能源故事,本质上是中国故事。”这一故事的核心,正是以清洁能源外交书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从“一带一路”到“全球南方”的绿色辐射。我国清洁能源外交是对“绿色丝绸之路”的深化实践,当前我国累计同100多个国家开展了清洁能源项目合作,覆盖光伏、风电、水电、储能等全产业链。例如,中企承建的阿联酋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项目,年供电20万户家庭,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40万吨,使阿联酋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13%。这些项目通过“建设—运营—本地化”的模式,为当地培养出优秀的清洁能源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并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科技创新。此外,我国清洁能源外交与“全球南方”深度绑定,面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我国清洁能源产能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实现资源互补与协同治理。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链需要印尼镍矿的支撑,同时我国也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在中东地区的市场,通过“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等机制,我国为印尼、越南等国提供绿色融资,破解190亿美元/年的资金缺口。这种合作打破了“中心—边缘”的传统分工体系,形成资源与技术的双向依赖,创制了“南南合作”的新范式。
从成本革命到经验共享的技术赋能。我国通过规模化生产与技术创新,降低了全球绿色转型的门槛,将光伏组件的成本降低80%,风电度电成本降低60%,清洁能源正在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我国供应了全球80%的光伏产品,2023年光伏组件的出口额超过2000亿元,帮助巴基斯坦等国光伏发电占比提升至5%-13%,并有效推动了电动汽车在当地的普及。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若排除中国产能,2023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将不足1吉瓦,远低于实际规模的117吉瓦。此外,清洁能源外交推动我国自主的清洁能源技术标准走向国际,中国制定的漂浮光伏设计规范被印尼等国采纳,成为东南亚国家的行业基准;中国分享的电力技术覆盖30多个国家,巴西的美丽山项目在采用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标准后,实现了2000公里的电力零损耗传输;中核集团在阿联酋推出的高温气冷堆模型等创新成果,推动中东核能合作从单一设备出口转向系统集成。这些技术标准的输出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事务中的话语权,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适配成本。
从项目合作到政策协调的机制创新。针对“全球南方”发展清洁能源的融资难题,我国探索出多元化模式来共担绿色金融风险。亚投行为印尼的光伏项目提供风险对冲,并降低中企的投资门槛;埃及苏伊士湾风电项目通过“中国贷款+本地股权”的混合融资机制,实现资金与责任共担;中国碳交易市场与东盟国家、海湾国家逐渐互联,积极探索跨境碳信用互认。同时,我国清洁能源外交注重区域治理平台构建,通过多边主义强化制度性合作。在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推动区域电网互联,促进老挝水电与泰国光伏优势互补;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牵头设立“清洁技术转移基金”,资助非洲国家建设小型光伏电站;推动建立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为信息沟通和产业合作提供对话平台,不断完善“全球南方”的政策工具箱。
我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本质是以技术普惠推动发展权再平衡。通过分享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方案,助力“全球南方”跨越“高碳增长陷阱”,并重构全球气候治理的正义性——减排不应是发达国家的道德特权,而是所有国家平等享有的发展权利。未来,我国仍需警惕地缘政治风险,强化中资清洁能源项目数据的透明度,突出就业、民生、环保等社会效益,回应西方炒作的不实论调;引入第三方企业参股项目建设,淡化“中国主导”的标签;加速产业链共建和人才联合培养,拓展新兴清洁能源领域合作;推广“能源互联网”经验,帮助更多国家实现能源智慧管理。我国将进一步把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标准体系的“软联通”相结合,在绿色金融、标准互认、区域协同等领域深化制度性合作,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正如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所言:“当今世界的能源故事,本质上是中国故事。”这一故事的核心,正是以清洁能源外交书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