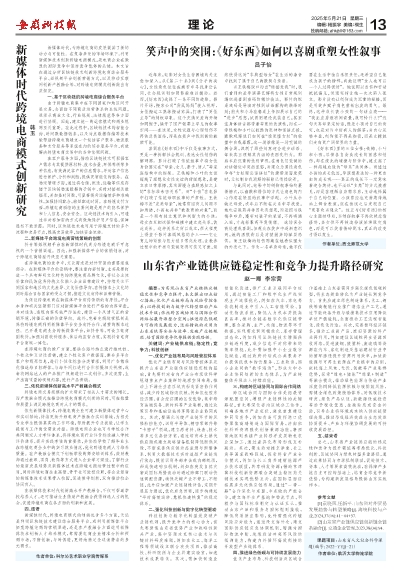发布日期:
笑声中的突围:《好东西》如何以喜剧重塑女性叙事
文章字数:1480
近年来,电影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愈加深入,从《第二十条》到《分手的决心》,女性角色往往在痛苦中寻找身份认同,社会规训则如阴影般难以撼动。然而,《好东西》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影片开场,搬家公司“袋鼠妈妈”驶入视野,女性搬运工熟练搬动家具,打破了“男性主导”的刻板印象。这个充满反差的开场如同楔子,撬开了国产银幕上罕见的叙事空间——在这里,女性议题与心理创伤不再被悲情渲染,而是在笑声中找到新的救赎可能。
喜剧在《好东西》中不仅是叙事方式,更是一种拆解社会规训、表达女性创伤的解码器。影片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将女性身份固定在“母亲、女儿、妻子、情人”等家庭结构中的框架。王铁梅和小叶的友谊超越了理想化女性友谊的甜腻想象,是建立在日常摩擦、真实困境与幽默感知之上的“非标准亲密关系”。而“小孩”在电影中打破了传统母职叙事的严肃性。王铁梅不是“完美母亲”,她常常因育儿问题不知所措,小孩也并非“被教育的对象”,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和判断力的个体。母女在互相试探和碰撞中建立起关系,彼此成长。这种关系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影片喜剧风格的介入——它让育儿的紧张与压力被日常化处理,让教养过程中的矛盾与荒诞变得可笑又可爱,最终使得这对“非典型母女”在生活的杂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默契与亲密。
当王铁梅脱口而出“链接发我”时,我们看到的是导演邵艺辉将女性日常规训编织进喜剧密码的精妙技法。影片的饭桌戏码是导演对性别话语解构的巅峰时刻:前夫和小马在餐桌上争相展示自己的“进步”思想,试图用理论武装自己,甚至连身体语言都带着夸张的表演性,而在一旁铁梅和小叶以狡黠的眼神和话语点拨,默默观察他们如何在“谁更懂女权”的较量中自我暴露,这一场景像是一场荒诞的舞台剧,讽刺了那些刻意迎合进步话语、却未真正理解其内涵的表面化行为。那些本应沉重的性别审视,在角色们荒诞的对话错位中突然显影,当观众为男性角色争夺“女权理论话语权”的滑稽场面发笑时,父权制自我消解的裂隙已悄然绽开。
与此同时,电影中的创伤叙事始终裹着糖衣,以幽默和错位的方式让角色的内心伤痕在轻盈的叙事中浮现。小叶从小缺乏母爱,成年后不断在关系中寻找爱,她吃安眠药并非因失恋想死,而是因与铁梅争吵后,遵守对孩子的承诺,不再喝酒入睡,才选择服药平复情绪。 这场误会被处理成喜剧,但观众在笑声中逐渐意识到,她的洒脱背后是对被抛弃的深层恐惧。而王铁梅的创伤则藏在她看似强大的外壳之下。作为一名单身母亲,她不仅要在生活中独自承担责任,还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向她证明“女人也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她试图以自信和行动抵抗偏见,但现实却让她一次次陷入孤立。影片没有让创伤成为沉重的桎梏,而是用笑声赋予角色重新出发的勇气。最终,这种成长被小孩的一句话点亮——“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这句天真却坚定的话,既是小孩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片中所有人的解答:当内心足够丰盈,创伤便不再是枷锁,而是支撑她们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力量。
《好东西》里的三位女性:铁梅、小叶和小孩,尽管各自背负成长的困惑和创伤,却在彼此的碰撞与陪伴中,建立起了一种超越血缘的“母系”共同体。而透过小孩的成长轨迹,导演想表达的一种更自由的成长观——真正的成长不一定意味着迎合期待,也不必以“主角”的方式被看见,而是在理解自身需求后,主动选择属于自己的位置。小孩曾经也充满期待地站上舞台表演,但在尝试之后发现自己“更喜欢当观众”。这正与《好东西》的核心主题相呼应,当创伤叙事不再依赖悲情修辞,当女性不再被迫扮演某种既定角色,而是可以笑着撕碎剧本,真正的改变才得以发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喜剧在《好东西》中不仅是叙事方式,更是一种拆解社会规训、表达女性创伤的解码器。影片打破了传统叙事中将女性身份固定在“母亲、女儿、妻子、情人”等家庭结构中的框架。王铁梅和小叶的友谊超越了理想化女性友谊的甜腻想象,是建立在日常摩擦、真实困境与幽默感知之上的“非标准亲密关系”。而“小孩”在电影中打破了传统母职叙事的严肃性。王铁梅不是“完美母亲”,她常常因育儿问题不知所措,小孩也并非“被教育的对象”,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和判断力的个体。母女在互相试探和碰撞中建立起关系,彼此成长。这种关系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影片喜剧风格的介入——它让育儿的紧张与压力被日常化处理,让教养过程中的矛盾与荒诞变得可笑又可爱,最终使得这对“非典型母女”在生活的杂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默契与亲密。
当王铁梅脱口而出“链接发我”时,我们看到的是导演邵艺辉将女性日常规训编织进喜剧密码的精妙技法。影片的饭桌戏码是导演对性别话语解构的巅峰时刻:前夫和小马在餐桌上争相展示自己的“进步”思想,试图用理论武装自己,甚至连身体语言都带着夸张的表演性,而在一旁铁梅和小叶以狡黠的眼神和话语点拨,默默观察他们如何在“谁更懂女权”的较量中自我暴露,这一场景像是一场荒诞的舞台剧,讽刺了那些刻意迎合进步话语、却未真正理解其内涵的表面化行为。那些本应沉重的性别审视,在角色们荒诞的对话错位中突然显影,当观众为男性角色争夺“女权理论话语权”的滑稽场面发笑时,父权制自我消解的裂隙已悄然绽开。
与此同时,电影中的创伤叙事始终裹着糖衣,以幽默和错位的方式让角色的内心伤痕在轻盈的叙事中浮现。小叶从小缺乏母爱,成年后不断在关系中寻找爱,她吃安眠药并非因失恋想死,而是因与铁梅争吵后,遵守对孩子的承诺,不再喝酒入睡,才选择服药平复情绪。 这场误会被处理成喜剧,但观众在笑声中逐渐意识到,她的洒脱背后是对被抛弃的深层恐惧。而王铁梅的创伤则藏在她看似强大的外壳之下。作为一名单身母亲,她不仅要在生活中独自承担责任,还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向她证明“女人也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她试图以自信和行动抵抗偏见,但现实却让她一次次陷入孤立。影片没有让创伤成为沉重的桎梏,而是用笑声赋予角色重新出发的勇气。最终,这种成长被小孩的一句话点亮——“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这句天真却坚定的话,既是小孩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片中所有人的解答:当内心足够丰盈,创伤便不再是枷锁,而是支撑她们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力量。
《好东西》里的三位女性:铁梅、小叶和小孩,尽管各自背负成长的困惑和创伤,却在彼此的碰撞与陪伴中,建立起了一种超越血缘的“母系”共同体。而透过小孩的成长轨迹,导演想表达的一种更自由的成长观——真正的成长不一定意味着迎合期待,也不必以“主角”的方式被看见,而是在理解自身需求后,主动选择属于自己的位置。小孩曾经也充满期待地站上舞台表演,但在尝试之后发现自己“更喜欢当观众”。这正与《好东西》的核心主题相呼应,当创伤叙事不再依赖悲情修辞,当女性不再被迫扮演某种既定角色,而是可以笑着撕碎剧本,真正的改变才得以发生。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