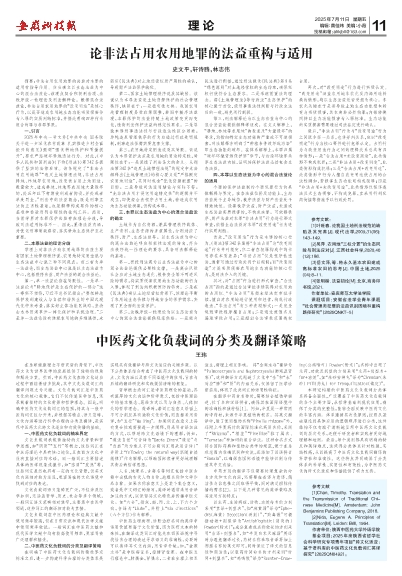发布日期:
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益重构与适用
文章字数:2672
摘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益对本罪的适用有指导作用。应当确立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该观点契合积极刑法观、法秩序统一性理论及刑法解释论。根据混合法益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改变用途”是核心行为,以是否造成农用地生态功能实质损害作为入罪的实质判断标准,并据此明确四种行为组合的罪与非罪界限。
一、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要求严惩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刑法》)第342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该条规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中的法益概念,既是刑事立法的正当性基础,也是解释构成要件的核心基准和检验刑罚合理性的批判工具。然而,当前学界对本罪保护法益存在理论分歧,导致司法适用标准不一。因此,厘清法益内涵,对优化刑事制裁路径、落实耕地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二、本罪法益的理论分歧
学理上对非法占有农用地罪的法益主要有国家土地管理秩序说、农用地特定用途说与生态法益中心说三种不同观点。前二者为单一法益论,而生态法益中心说是以生态法益为中心,包括秩序法益、财产法益的混合法益论。
第一,单一法益论存在局限性。一是单一法益论与“耕地保护是生态保护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不相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耕地保护放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来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二是单一法益论没有体现农用地的多维属性,未回应《民法典》对土地经营权财产属性的确认,导致财产法益保护缺位。
第二,国家土地管理秩序说及其缺陷。该说认为本罪法益是土地资源保护的社会管理秩序,缺陷在于:一是稳定性欠缺。我国农用地管理制度易受政策调整,若固守秩序法益观,本罪保护的法益将随土地政策变更而变化,违背刑法保护法益的稳定性要求。二是导致本罪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区分困难。单纯违反管理秩序的行为应通过行政处罚规制,刑事违法性需实质危害支撑。
第三,农用地特定用途说及其局限。该说认为本罪保护法益是农用地的用途特定性,局限性在于:一是误读了刑法条文的含义。从刑法第342条“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规定中无法解释出《土地管理法》的核心要义是“严格限定农用地用途”,其同时包含“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二是导致司法适用结论与实际不符。“先非法占用才侵犯用途特定性”的逻辑并不成立,即使经合法程序占用土地,若造成农用地生态功能损害,仍构成本罪。
三、本罪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的确立
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兼具管理秩序载体、生产资料、生态资源的多重属性,分别对应了秩序、财产、生态法益等。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呼应积极性法观的转向、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理论的要求、具备刑法解释论的基础。
第一,积极刑法观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提供必要性支撑。一是契合风险社会应对土地生态退化、粮食安全等不可逆风险的需求,将实质侵害农用地生态功能的行为入罪,体现了刑法向积极预防的转向。二是在《民法典》确认土地经营权背景下,该理论平衡了农用地生态价值与耕地安全的保护需求,实现了更全面的法益保护。
第二,法秩序统一性理论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提供规范供给。一是能与民法进行衔接,通过刑法强化《民法典》第9条“绿色原则”对土地经营权的生态约束,确保私权行使符合生态要求。二是承继前置法的理念。将《土地管理法》等行政法“生态保护”的核心置于首位,使刑事违法性判断与行政立法目的一致,避免刑行割裂。
第三,刑法解释论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提供解释学证成。在文义解释上,“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表述及“大量毁坏”的要求,均指向特定生态功能的严重或不可逆损害,司法解释亦明确了“种植条件毁坏或污染”即生态功能的破坏。在体系解释上,本罪归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章节,与污染环境罪共享生态法益内核,证明其保护法益必然包含生态法益。
四、本罪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的适用
个罪的保护法益制约个罪犯罪行为的具体解释与界定。在各法益位阶及功能上,生态法益处于主导地位,秩序法益与财产法益处于辅助地位。侵害秩序法益、财产法益,未造成生态法益实质损害的,不构成本罪。可依据秩序、财产法益对本罪“非法占用”行为进行形式审查,依据生态法益对本罪“改变用途”行为进行实质判断。
首先,“改变用途”行为是本罪的核心行为。《刑法》第342条虽将“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行为并列规定,但二者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存在本质差异:“非法占用”仅是程序性违法,通常可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规制;而“改变用途”才是实质侵害农用地生态功能的核心行为,是刑法介入的关键。
其次,对“占用”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合法占用”指的是通过合法审批手续获得对农用地的占用权。“非法占用”系指未经法定审批手续,擅自对农用地进行使用和经营,构成行政违法。“非法占用”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完全规避审批程序擅自占用;二是通过虚假名义骗取审批占用;三是超出合法审批范围越权占用。
再次,对“改变用途”行为进行实质认定。“改变用途”涵盖农用地非农化及内部用途转换的情形,均以生态法益是否受损为核心。非农化关键在于是否导致土地生态功能根本转变与实质损害,其本身非必然构罪;内部转换同样以生态功能损害为入罪标准。生态功能的实质损害需要通过司法鉴定进行确认。
最后,“非法占用”行为与“改变用途”行为之间既非择一关系,也非并列关系,应以“改变用途”行为为核心要件进行犯罪认定。占用行为与改变用途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总共有四种情形:一是“合法占用+未改变用途”,此类情形不构成犯罪;二是“非法占用+改变用途”,此类情形构成犯罪;三是“合法占用+改变用途”,此类情形中行为人擅自改变用途使占用的合法性阙如,若损害生态功能则构成犯罪;四是“非法占用+未改变用途”,此类情形仅程序违法且无生态损害,不构成犯罪,宜采用行刑反向衔接等措施予以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1]叶旺春.论我国土地刑法规范的缺陷及其完善[J].现代法学,2009,31(06):143-149.
[2]吴萍.农用地“三权分置”的生态风险与刑法应对[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12):186.
[3]岳文泽,等.将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思考[J].中国土地,2025(04):8-11.
[4]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
课题项目:安徽省法学会青年课题“社会管理类犯罪的法益识别困境和重构路径研究”(2025QNKT-5)
一、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要求严惩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刑法》)第342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该条规定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中的法益概念,既是刑事立法的正当性基础,也是解释构成要件的核心基准和检验刑罚合理性的批判工具。然而,当前学界对本罪保护法益存在理论分歧,导致司法适用标准不一。因此,厘清法益内涵,对优化刑事制裁路径、落实耕地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二、本罪法益的理论分歧
学理上对非法占有农用地罪的法益主要有国家土地管理秩序说、农用地特定用途说与生态法益中心说三种不同观点。前二者为单一法益论,而生态法益中心说是以生态法益为中心,包括秩序法益、财产法益的混合法益论。
第一,单一法益论存在局限性。一是单一法益论与“耕地保护是生态保护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不相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耕地保护放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来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二是单一法益论没有体现农用地的多维属性,未回应《民法典》对土地经营权财产属性的确认,导致财产法益保护缺位。
第二,国家土地管理秩序说及其缺陷。该说认为本罪法益是土地资源保护的社会管理秩序,缺陷在于:一是稳定性欠缺。我国农用地管理制度易受政策调整,若固守秩序法益观,本罪保护的法益将随土地政策变更而变化,违背刑法保护法益的稳定性要求。二是导致本罪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区分困难。单纯违反管理秩序的行为应通过行政处罚规制,刑事违法性需实质危害支撑。
第三,农用地特定用途说及其局限。该说认为本罪保护法益是农用地的用途特定性,局限性在于:一是误读了刑法条文的含义。从刑法第342条“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的规定中无法解释出《土地管理法》的核心要义是“严格限定农用地用途”,其同时包含“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二是导致司法适用结论与实际不符。“先非法占用才侵犯用途特定性”的逻辑并不成立,即使经合法程序占用土地,若造成农用地生态功能损害,仍构成本罪。
三、本罪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的确立
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兼具管理秩序载体、生产资料、生态资源的多重属性,分别对应了秩序、财产、生态法益等。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呼应积极性法观的转向、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理论的要求、具备刑法解释论的基础。
第一,积极刑法观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提供必要性支撑。一是契合风险社会应对土地生态退化、粮食安全等不可逆风险的需求,将实质侵害农用地生态功能的行为入罪,体现了刑法向积极预防的转向。二是在《民法典》确认土地经营权背景下,该理论平衡了农用地生态价值与耕地安全的保护需求,实现了更全面的法益保护。
第二,法秩序统一性理论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提供规范供给。一是能与民法进行衔接,通过刑法强化《民法典》第9条“绿色原则”对土地经营权的生态约束,确保私权行使符合生态要求。二是承继前置法的理念。将《土地管理法》等行政法“生态保护”的核心置于首位,使刑事违法性判断与行政立法目的一致,避免刑行割裂。
第三,刑法解释论为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提供解释学证成。在文义解释上,“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表述及“大量毁坏”的要求,均指向特定生态功能的严重或不可逆损害,司法解释亦明确了“种植条件毁坏或污染”即生态功能的破坏。在体系解释上,本罪归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章节,与污染环境罪共享生态法益内核,证明其保护法益必然包含生态法益。
四、本罪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混合法益论的适用
个罪的保护法益制约个罪犯罪行为的具体解释与界定。在各法益位阶及功能上,生态法益处于主导地位,秩序法益与财产法益处于辅助地位。侵害秩序法益、财产法益,未造成生态法益实质损害的,不构成本罪。可依据秩序、财产法益对本罪“非法占用”行为进行形式审查,依据生态法益对本罪“改变用途”行为进行实质判断。
首先,“改变用途”行为是本罪的核心行为。《刑法》第342条虽将“非法占用”与“改变用途”行为并列规定,但二者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存在本质差异:“非法占用”仅是程序性违法,通常可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规制;而“改变用途”才是实质侵害农用地生态功能的核心行为,是刑法介入的关键。
其次,对“占用”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合法占用”指的是通过合法审批手续获得对农用地的占用权。“非法占用”系指未经法定审批手续,擅自对农用地进行使用和经营,构成行政违法。“非法占用”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完全规避审批程序擅自占用;二是通过虚假名义骗取审批占用;三是超出合法审批范围越权占用。
再次,对“改变用途”行为进行实质认定。“改变用途”涵盖农用地非农化及内部用途转换的情形,均以生态法益是否受损为核心。非农化关键在于是否导致土地生态功能根本转变与实质损害,其本身非必然构罪;内部转换同样以生态功能损害为入罪标准。生态功能的实质损害需要通过司法鉴定进行确认。
最后,“非法占用”行为与“改变用途”行为之间既非择一关系,也非并列关系,应以“改变用途”行为为核心要件进行犯罪认定。占用行为与改变用途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总共有四种情形:一是“合法占用+未改变用途”,此类情形不构成犯罪;二是“非法占用+改变用途”,此类情形构成犯罪;三是“合法占用+改变用途”,此类情形中行为人擅自改变用途使占用的合法性阙如,若损害生态功能则构成犯罪;四是“非法占用+未改变用途”,此类情形仅程序违法且无生态损害,不构成犯罪,宜采用行刑反向衔接等措施予以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1]叶旺春.论我国土地刑法规范的缺陷及其完善[J].现代法学,2009,31(06):143-149.
[2]吴萍.农用地“三权分置”的生态风险与刑法应对[J].江西社会科学,2020,40(12):186.
[3]岳文泽,等.将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思考[J].中国土地,2025(04):8-11.
[4]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
课题项目:安徽省法学会青年课题“社会管理类犯罪的法益识别困境和重构路径研究”(2025QNK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