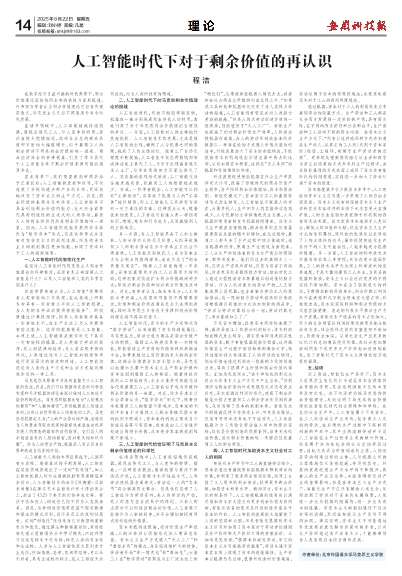发布日期:
人工智能时代下对于剩余价值的再认识
文章字数:5312
在数字经济日益兴盛的时代背景下,剩余价值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发展机遇。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已经丧失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时代发展。
在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超越传统机器,展现出替代工人、与人竞争的特质,劳动者被大规模取代,然而社会总的商品价值却不断地大幅度增长,似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经济社会的种种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刻审视并给予正面回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不仅造就了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更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也无法全面替代具有创造性的生成式的人类劳动,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资本转化为“数字资本”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而是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属性更加隐蔽,加深了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程度。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化生产
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时,必须首先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以及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是要探索人类智能的工作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机器,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智能服务”。即机器通过计算机程序,探索人类智能并具备一定智能水平,在生产生活上为人类提供智能化服务。这样的机器就是人工智能。本质上说,人工智能就是数字时代下具有一定智能性的机器,是人类脑力劳动的延伸,是人的机体的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人类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对物质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改造。人工智能仍然是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解放作用的一种工具。
马克思在其原著中并没有直接关于人工智能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和关于机器的理论来探讨他对人工智能可能持有的观点。马克思将机器比喻为“人的意志的器官”和“人脑的器官”,表明机器是人创造出来的,旨在让自然界顺从人的意志的工具。马克思将机器定义为:“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作为人的劳动产物,机器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手段。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脑具有生成性。随着算法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展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如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围棋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创作的画作《埃德蒙·贝拉米画像》在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43.25万美元的价格并成交等。都似乎告知世人,创造性已经不再为人类所独有。但是,这种创造性通常是基于现有数据和算法的模式识别,而不是真正的原创性思考。AI的“创造性”往往是对已有数据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通过算法和数据驱动的,虽然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并从中学习模式,但这种学习往往是特定于任务的,缺乏人类的灵活性和生成性。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成性,例如情感、思考、意识等范畴,可以从无到有,具有生成性的特征,是人工智能无法到达的,而为人类所独有的领域。
二、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不断取得新突破,机器在一部分领域展现出替代人的特质,由此引发了对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合理性的争议。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地位发起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的出现,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挑战了人的主体地位。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工智能不仅在骨骼肌肉等肉体功能上替代了人,乃至于出现高智能化无人工厂,似乎在思维智力层面也替代了人。其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工厂智能化设备越来越完善,而雇佣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可以拥有“主体意识”,这导致了机器与人的“主客体”地位颠倒,即人工智能从工具转变为具有一定主体性的实体。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像人类一样拥有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能力,从而威胁到人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当人工智能具备了人的主体性,人的活劳动已经无足轻重,从而导致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再重要,人工智能反而取代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源泉,由此引发了“剩余价值无用论”。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雇佣更少的工人以图更大的利润,这种现象对传统扩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造成冲击。对此,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水平极高,人类很有可能将不再需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商品社会无法得到表现,那时马克思主义有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将不再具有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的生产方式转化为“数字劳动”,从而消解了资本的剥削属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雇佣工人的劳动具有一种特殊性,即能够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并带来超过工资价值的更大的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马克思以此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随着科技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大量使用智能化设备代替雇佣工人,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另一来源。对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者认为,“数字劳动”形式下,随着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数量不断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中来自于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比例不断减小,资本家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智能设备等不变资本,或者是由人工智能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家的剥削程度不断减小。
三、人工智能时代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在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超越传统机器,展现出替代工人、与人竞争的特质。据此,一些研究者提出,随着数据与算法不断迭代升级,人工智能化水平远超今天,人类劳动被机器全面替代,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将会脱离历史舞台。但是他们忽视了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资料,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意志在自然界中的体现。只有人的活劳动可以创造出商品的价值,人工智能只能够作为人脑的延伸,并不会增加相同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价值生产率提高,人的活劳动以间接形式加入商品总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无人工厂”和“虚拟车间”的模式,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劳动者开始“单一模式化”和“离场化”,大量工人在“数字劳动”前期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后期被智能机器人替代失业,被排挤在社会商品总价值的创造过程之外。“如果说工具时代和机器时代完成了对人类体力劳动的超越,人工智能则有望完成对人类脑力劳动的超越。”但是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般规律,仍然适用于“无人工厂”。智能生产线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效率,人的劳动被机器所遮蔽,由人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量以一种潜在性的方式进入价值总量的创造中,科技发展加大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在价值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而加剧资本积累,这就是“无人车间”的机器和价值增值的秘密。
科技发展促使智能机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提高了智能时代的商品价值产生效率,资产阶级剩余价值增加、资本积累加剧。智能化模式下,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劳动形式发生转变,人工智能似乎脱离人的存在,大量替代人,生产环节人的直接劳动急剧减少,人与机器的主客体角色发生互换,人从机器的使用者转变为机器的附庸者。资本主义生产效益显著提高,商品世界的总价值量随着商品总量的增大而增加,在此过程中,雇佣工人却失去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成为机器的附件,脱离生产过程成为旁观者。工人从生产的创造者转变为生产背后的管理者、程序开发者。他们同过去的雇佣工人一样,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前者更多的是提供体力劳动,智能时代工人通过无偿提供资本积累最具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劳动产物,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机器,包含着脑力劳动工人的原始劳动,这一原始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智能机器以间接的方式添加到新的商品中,“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
不变资本增加,促使资本周转的速度下降,最终导致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资本利润构成模式发生转变。固定资本即用来购买机器的资本,赋予智能机器超高价值量,这种高价值在生产过程不断被转移到商品之中,转移过程的持久性遮蔽了人的劳动的在场性,剩余价值也通过利润这一隐蔽的方式被创造出来,导致了机器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觉。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但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家通过利润的形式,遮蔽了剩余价值是无偿占用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得到的事实,从而消解了资本的剥削本性。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不变资本上升、可变资本降低,但是可变资本没有也不可能消失,人工智能机器作为人类物化劳动嵌入其中的劳动资料,仅仅是价值创造的物质条件,自身无法创造价值,因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仍然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四、人工智能时代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剥削
智能化生产环节中工人的直接劳动减少,资本家通过普遍使用智能机器来降低商品的价值,却积累了更多商品使用价值,实质上占据了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加剧资本积累水平。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工智能机器的使用是以满足增加资本家无偿占有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智能化设备的使用及科技的进步服务于资本的利益。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肢体和大脑,但是智能化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加剧了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劳动从属于资本在本质上体现了资本的剥削属性。生产资本以机器形态出场,机器所包含的价值越高,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就越高,也就意味着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程度越高。
通过机器,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转变为非雇佣劳动的隐蔽方式。生产劳动和工人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中,生产劳动和工人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更多的处理数据的脑力从业者和数字化劳工以隐蔽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采取非雇佣的方式表面上减轻了资本在智能时代的剥削程度,实则进一步加大了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
资本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在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下无法在更大范围扩散,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囿于私有制的存在而无法实现。技术发展本应造福于人类社会,解放人的四肢和大脑,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属性,使科技的发展反过来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最终促使智能化生产条件下的人丧失能动性,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科学技术为少数资本家私人手掌握,无法在更大范围扩散,工人的技术水平无法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于是大量的雇佣工人失业,为更多的机器所替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不断推动新的科技革命,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外在表现形式不断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科技愈发达,资本家获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方式愈直接便捷。发达的科技水平推动生产力水平发展,智能化生产设备的资本占比加大,巨大的社会财富以利润的形式被更多地分配给资本家,社会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阶级对立加深。从而社会生产出更多数以亿计的总的商品使用价值,在社会愈加繁荣的阴影下是更多无产阶级愈加贫困的底色,成了智能时代下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五、结语
综上所述,智能化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不仅没有动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反而证明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智能化时代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总的社会生产中,人工智能属于不变资本,是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包含着工人先前的劳动,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不断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其产生的高额劳动并不是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生成的额外价值,而是属于其内在包含的社会总的劳动过程,因此无法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人仍然是劳动创造过程的主体,人与机器之间的主客体地位只是被遮蔽,并没有改变。科技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改善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当然值得肯定其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智能化生产不仅没有解放人类社会,反而加剧了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程度,人更进一步沦为机器的附属物,进一步沦为资本的傀儡。而资本主义的剥削属性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在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得到加剧。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科技发展自发化解自身固有的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够带领全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超越传统机器,展现出替代工人、与人竞争的特质,劳动者被大规模取代,然而社会总的商品价值却不断地大幅度增长,似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经济社会的种种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条件下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的激烈争论。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刻审视并给予正面回应: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不仅造就了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更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也无法全面替代具有创造性的生成式的人类劳动,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资本转化为“数字资本”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而是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属性更加隐蔽,加深了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程度。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化生产
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时,必须首先正确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以及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是要探索人类智能的工作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具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机器,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智能服务”。即机器通过计算机程序,探索人类智能并具备一定智能水平,在生产生活上为人类提供智能化服务。这样的机器就是人工智能。本质上说,人工智能就是数字时代下具有一定智能性的机器,是人类脑力劳动的延伸,是人的机体的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人类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对物质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改造。人工智能仍然是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解放作用的一种工具。
马克思在其原著中并没有直接关于人工智能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和关于机器的理论来探讨他对人工智能可能持有的观点。马克思将机器比喻为“人的意志的器官”和“人脑的器官”,表明机器是人创造出来的,旨在让自然界顺从人的意志的工具。马克思将机器定义为:“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作为人的劳动产物,机器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手段。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脑具有生成性。随着算法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展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如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围棋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创作的画作《埃德蒙·贝拉米画像》在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43.25万美元的价格并成交等。都似乎告知世人,创造性已经不再为人类所独有。但是,这种创造性通常是基于现有数据和算法的模式识别,而不是真正的原创性思考。AI的“创造性”往往是对已有数据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通过算法和数据驱动的,虽然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并从中学习模式,但这种学习往往是特定于任务的,缺乏人类的灵活性和生成性。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最大区别在于生成性,例如情感、思考、意识等范畴,可以从无到有,具有生成性的特征,是人工智能无法到达的,而为人类所独有的领域。
二、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不断取得新突破,机器在一部分领域展现出替代人的特质,由此引发了对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合理性的争议。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地位发起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强人工智能的出现,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挑战了人的主体地位。随着工厂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工智能不仅在骨骼肌肉等肉体功能上替代了人,乃至于出现高智能化无人工厂,似乎在思维智力层面也替代了人。其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工厂智能化设备越来越完善,而雇佣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可以拥有“主体意识”,这导致了机器与人的“主客体”地位颠倒,即人工智能从工具转变为具有一定主体性的实体。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像人类一样拥有知识、情感、意志和行为能力,从而威胁到人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当人工智能具备了人的主体性,人的活劳动已经无足轻重,从而导致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再重要,人工智能反而取代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源泉,由此引发了“剩余价值无用论”。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家雇佣更少的工人以图更大的利润,这种现象对传统扩大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造成冲击。对此,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社会,人工智能水平极高,人类很有可能将不再需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商品社会无法得到表现,那时马克思主义有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将不再具有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的生产方式转化为“数字劳动”,从而消解了资本的剥削属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雇佣工人的劳动具有一种特殊性,即能够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并带来超过工资价值的更大的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马克思以此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随着科技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企业大量使用智能化设备代替雇佣工人,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另一来源。对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者认为,“数字劳动”形式下,随着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数量不断减少,资本家的利润中来自于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比例不断减小,资本家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智能设备等不变资本,或者是由人工智能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家的剥削程度不断减小。
三、人工智能时代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
在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超越传统机器,展现出替代工人、与人竞争的特质。据此,一些研究者提出,随着数据与算法不断迭代升级,人工智能化水平远超今天,人类劳动被机器全面替代,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将会脱离历史舞台。但是他们忽视了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资料,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意志在自然界中的体现。只有人的活劳动可以创造出商品的价值,人工智能只能够作为人脑的延伸,并不会增加相同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价值生产率提高,人的活劳动以间接形式加入商品总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无人工厂”和“虚拟车间”的模式,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劳动者开始“单一模式化”和“离场化”,大量工人在“数字劳动”前期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后期被智能机器人替代失业,被排挤在社会商品总价值的创造过程之外。“如果说工具时代和机器时代完成了对人类体力劳动的超越,人工智能则有望完成对人类脑力劳动的超越。”但是人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般规律,仍然适用于“无人工厂”。智能生产线提高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效率,人的劳动被机器所遮蔽,由人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量以一种潜在性的方式进入价值总量的创造中,科技发展加大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在价值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而加剧资本积累,这就是“无人车间”的机器和价值增值的秘密。
科技发展促使智能机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提高了智能时代的商品价值产生效率,资产阶级剩余价值增加、资本积累加剧。智能化模式下,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劳动形式发生转变,人工智能似乎脱离人的存在,大量替代人,生产环节人的直接劳动急剧减少,人与机器的主客体角色发生互换,人从机器的使用者转变为机器的附庸者。资本主义生产效益显著提高,商品世界的总价值量随着商品总量的增大而增加,在此过程中,雇佣工人却失去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成为机器的附件,脱离生产过程成为旁观者。工人从生产的创造者转变为生产背后的管理者、程序开发者。他们同过去的雇佣工人一样,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前者更多的是提供体力劳动,智能时代工人通过无偿提供资本积累最具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劳动产物,人工智能本质上是机器,包含着脑力劳动工人的原始劳动,这一原始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被智能机器以间接的方式添加到新的商品中,“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
不变资本增加,促使资本周转的速度下降,最终导致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资本利润构成模式发生转变。固定资本即用来购买机器的资本,赋予智能机器超高价值量,这种高价值在生产过程不断被转移到商品之中,转移过程的持久性遮蔽了人的劳动的在场性,剩余价值也通过利润这一隐蔽的方式被创造出来,导致了机器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觉。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但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家通过利润的形式,遮蔽了剩余价值是无偿占用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得到的事实,从而消解了资本的剥削本性。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促使不变资本上升、可变资本降低,但是可变资本没有也不可能消失,人工智能机器作为人类物化劳动嵌入其中的劳动资料,仅仅是价值创造的物质条件,自身无法创造价值,因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仍然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四、人工智能时代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剥削
智能化生产环节中工人的直接劳动减少,资本家通过普遍使用智能机器来降低商品的价值,却积累了更多商品使用价值,实质上占据了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加剧资本积累水平。概而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工智能机器的使用是以满足增加资本家无偿占有更多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智能化设备的使用及科技的进步服务于资本的利益。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肢体和大脑,但是智能化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加剧了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劳动从属于资本在本质上体现了资本的剥削属性。生产资本以机器形态出场,机器所包含的价值越高,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就越高,也就意味着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程度越高。
通过机器,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转变为非雇佣劳动的隐蔽方式。生产劳动和工人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中,生产劳动和工人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更多的处理数据的脑力从业者和数字化劳工以隐蔽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采取非雇佣的方式表面上减轻了资本在智能时代的剥削程度,实则进一步加大了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
资本高度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在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下无法在更大范围扩散,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囿于私有制的存在而无法实现。技术发展本应造福于人类社会,解放人的四肢和大脑,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属性,使科技的发展反过来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最终促使智能化生产条件下的人丧失能动性,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科学技术为少数资本家私人手掌握,无法在更大范围扩散,工人的技术水平无法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于是大量的雇佣工人失业,为更多的机器所替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不断推动新的科技革命,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外在表现形式不断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科技愈发达,资本家获取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方式愈直接便捷。发达的科技水平推动生产力水平发展,智能化生产设备的资本占比加大,巨大的社会财富以利润的形式被更多地分配给资本家,社会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阶级对立加深。从而社会生产出更多数以亿计的总的商品使用价值,在社会愈加繁荣的阴影下是更多无产阶级愈加贫困的底色,成了智能时代下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五、结语
综上所述,智能化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不仅没有动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反而证明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智能化时代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总的社会生产中,人工智能属于不变资本,是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包含着工人先前的劳动,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不断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其产生的高额劳动并不是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生成的额外价值,而是属于其内在包含的社会总的劳动过程,因此无法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人仍然是劳动创造过程的主体,人与机器之间的主客体地位只是被遮蔽,并没有改变。科技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改善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当然值得肯定其产生的重要影响,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智能化生产不仅没有解放人类社会,反而加剧了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程度,人更进一步沦为机器的附属物,进一步沦为资本的傀儡。而资本主义的剥削属性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在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得到加剧。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科技发展自发化解自身固有的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够带领全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