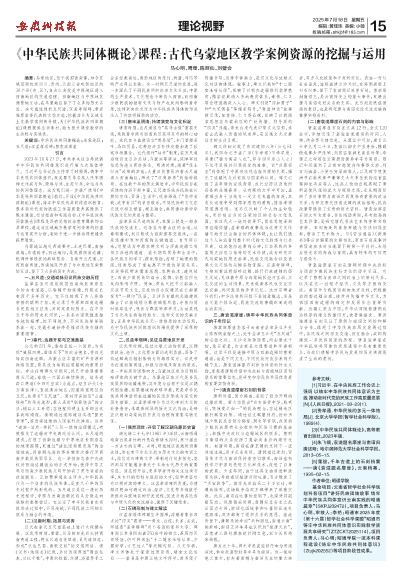发布日期: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古代乌蒙地区教学案例资源的挖掘与运用
文章字数:5538
摘要:乌蒙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如今区域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毗邻地区的38个县(市、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进入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频繁地互动,在乌蒙地区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名迹。本文通过剖析五尺道、汉孟孝琚碑、唐袁滋摩崖等代表性文物史迹,挖掘其作为区域本土化教学案例的价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提供生动素材,助力提升课堂教学的生动性与实效性。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乌蒙地区;五尺道;汉孟孝琚碑;唐袁滋摩崖
引言
2023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为我们进一步推广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行动指南和实践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的公共课程,通过对区域地方教学案例资源的挖掘与运用展开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课程建设提质增效。
乌蒙地区地处西南要冲,北连巴蜀,南接滇越,东通黔中,西达缅印,是巩固西南边疆、抵御外部侵扰的战略前沿。自秦开五尺道、汉筑西南夷道,西南地区开启了与中原地区频繁的互动,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名迹。
一、五尺道:交通动脉见证民族交融历程
盐津县五尺道是我国西南地区保存至今的古老道路,从秦朝开始修建,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不仅体现了古人修路架桥的聪明才智,更记录了中原和西南边疆各民族相互往来、共同发展的历史。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条条古道就像连接各地的纽带,把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交通古道始终是推动民族交融的重要纽带。
(一)秦代:边疆开拓与交通奠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威服四夷,君临天下”的政治抱负,将目光转向西南边疆。乌蒙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战略位置,使其成为秦朝拓展疆域的重要目标。李冰任蜀郡太守期间,就已开始修建修筑五尺道,秦统一六国后继续修筑。这条道路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起点,经豆沙关(今云南盐津),直抵滇池地区,因道路宽度仅约五尺,故得名“五尺道”。面对西南地区“山崖险峻”的恶劣地形,秦人采用“积薪烧岩”的方法,辅以人工开凿,在绝壁间硬生生开辟出这条战略通道。秦朝通过道路建设实现“置吏管理”,将西南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这种“道路-治所-移民”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有效强化了边疆对中央的政治认同。五尺道的建成,打破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长期存在的地理阻隔,更通过“诸此国颇置吏焉”的治理措施,将秦朝先进的郡县制首次推行至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统治的正式开始,使得中原文明与西南少数民族文明开始有了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五尺道正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西南边疆民族从分散走向联结的重要物证。它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与融合的开端。
(二)汉唐时期:拓展与完善
汉代在秦代五尺道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拓展。汉武帝时期,唐蒙、司马相如先后主持西南夷道工程,将五尺道与夜郎道、灵关道相连,形成“北达巴蜀、南抵交趾”的交通网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西南夷道“商旅往来,日以千数”,中原的铁器、丝绸、漆器等手工业品经此南运,滇黔地区的筇竹、枸酱、马匹等特产也得以北输。这一时期五尺道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互动,中原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不断传入西南,而西南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与物产也反向影响着中原,这种双向的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注入了持续而强劲的动力。
(三)唐宋至明清:持续演变与文化积淀
唐宋时期,五尺道成为“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承载着中原与西南地区茶马互市的核心功能。宋代在今盐津设立“博易场”,专门管理茶叶、马匹贸易,这种经济互补性交换加速了区域市场整合。元代推行“站赤”制度,在五尺道沿线设立豆沙关站、乌蒙站等驿站,保障军政信息传递与商旅安全。明清时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大量汉族移民沿着五尺道涌入西南地区,形成了“汉夷杂居”的独特格局。在这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内涵不断丰富,五尺道沿线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贸易、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盐津县五尺道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各民族的交流史。这条在乌蒙山区的古道,从秦朝建成,到汉朝成为西南重要交通线,一直是连接中原和西南的关键通道。自开辟以来,它便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南边疆文明相互渗透的通道。在长期的贸易和生活中,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帮助,打破了地理的隔阂,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紧密关系。汉族移民带来儒家思想、农耕技术、建筑技艺,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歌舞、宗教信仰也反向影响中原。例如,彝族火把节习俗融入汉族节庆文化,汉族的四合院建筑在云南演变为“一颗印”民居。豆沙关古镇的关隘建筑融合了汉族城楼与彝族碉楼风格,寺庙内同时供奉孔子、观音与彝族毕摩神灵,生动展现了文化共生的独特魅力。这种文化的交融互鉴,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汉孟孝琚碑:见证乌蒙地区开发
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汉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达到鼎盛,具备了向边疆地区辐射影响力的雄厚实力。汉武帝为打通西南夷道,加强与西域及南亚的联系,进一步拓展帝国影响力,乌蒙地区成为汉朝经略西南的关键节点。乌蒙地区在汉代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带,其开发与治理不仅是汉朝巩固边疆、拓展疆域的战略举措,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与深化的历史缩影。汉孟孝琚碑作为汉代碑刻文化的珍贵遗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汉朝对乌蒙地区开发与治理的重要实物见证。
(一)偶然现世:开启了解汉朝乌蒙历史窗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深秋,云南昭通城南白泥井村的村民在修缮水沟时,意外掘出一方古朴的石碑。当时,昭通地区虽地处西南边陲,但也有不少关注地方历史文化的有识之士,他们对石碑的文字、形制进行初步探究,意识到其可能蕴含着关于本地古代历史的重要信息。消息传开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这块石碑,其古朴的形制与斑驳的文字,经学者鉴定为汉朝时期的碑文。汉孟孝琚碑的发现,为理解汉朝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手段推动乌蒙地区的开发进程,促进当地各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关键线索。
(二)石碑形制与碑文解读
汉孟孝琚碑碑额呈半圆形,浮雕着象征四方的“四灵”图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环绕着“孟孝琚碑”四个苍劲的篆书大字。碑身则以隶书阴刻着260余字的铭文,虽历经风雨侵蚀,仍可辨识出“十二随官未喻从师,少孺好学,才艺过人”等关键句段。从文字看,碑文书体处于篆隶过渡阶段,暗含文化适应 ——篆书是中原正统文字符号,隶书便于传播书写,这种字体融合,是汉文化与边疆文化对话的体现。叙事上,碑文记载的“十二随官未喻从师”,反映了汉朝在边疆推行儒学教育,儒家经典纳入当地教育体系,孝悌、仁义等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碑文引用“四知君子”和“六艺俱备”等儒家符号,“孝道神化”故事被记录,如孝悌、仁义等品德,反映了汉朝儒家思想在乌蒙地区的广泛传播。符号层的“四灵”浮雕,青龙白虎代表中原文化信仰,朱雀玄武融入西南地域崇拜,是汉越文化交叠设计的生动呈现。
碑文详细记载了东汉建初六年(公元81年),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不幸早逝,其妻(“犍为南安人也”,即今四川乐山人士)不远千里将其归葬祖茔的故事。而“归葬祖茔”则体现了中原宗法观念在乌蒙的扎根,强化了边疆民众对家族与国家的认同。碑文记述了孟孝琚的家族背景、成长经历以及他所具备的品德修养。从有限的文字中可知,孟孝琚出身于当地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家族,其成长过程中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推崇孝悌等道德准则。这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生命轨迹,更折射出当时乌蒙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在汉代大一统的背景下,儒家思想逐渐向边疆传播,孟孝琚的故事成为这种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具体体现,也让我们透过个人命运看到整个时代的文化脉络与社会风尚。这块饱经沧桑的石碑,以其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与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研究汉代乌蒙地区历史沿革、民族交流融合以及丧葬文化习俗的关键实物证据。汉孟孝琚碑,它铭刻着汉朝经略边疆、推行行政建制的历史足迹,见证着中原与乌蒙地区经济互动、文化交流的生动图景,更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的珍贵记忆。这方石碑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个体命运、民族交流故事编织而成的生动实践。
三、唐袁滋摩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千年印记
唐袁滋摩崖坐落于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山路西侧崖壁之上,处于盐津豆沙关“五尺道”的必经之处。豆沙关地势险要,两山壁立千仞,危石若悬,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里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也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交流往来的关键节点。唐袁滋摩崖石刻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承载着唐朝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南地区密切联系的重要信息,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唐袁滋摩崖石刻的背景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采取了较为开明的边疆政策。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在边疆地区推行羁縻政策。通过设立羁縻州府,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在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加强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唐朝与南诏的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演变过程。初唐时期,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一统洱海流域,双方关系友好。唐朝通过册封、贸易等方式与南诏保持着密切联系,南诏也积极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天宝年间,由于边将贪功冒进和政策失误,导致南诏叛唐归附吐蕃,双方爆发了“天宝战争”。唐军先后派兵二十万征讨,却遭致惨败,这场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深重灾难。此后,南诏在吐蕃的控制下,也深受其剥削压迫。到唐德宗时期,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大损,南诏也因战争和吐蕃的压迫处境艰难,双方都有了缓和关系的意愿。在此背景下,唐朝采纳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的战略,南诏王异牟寻也认识到“叛唐无益”,派使者三路赴唐表达归附之意,双方关系迎来转机。
唐贞元十年,御史中丞袁滋被任命为册南诏使,奉命赴滇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这一使命意义重大,标志着唐朝与南诏关系的重大转折,双方从此恢复和平友好交往。袁滋一行从长安出发,途经盐津豆沙关时,在路侧岩壁上刊石纪事,留下了袁滋题记摩崖石刻。重新册封南诏王,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映出唐与南诏友好关系的史实。此石刻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研究唐与南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唐袁滋摩崖石刻的内容与影响
唐袁滋摩崖石刻正文共12行,全文120余字,详细记录了袁滋出使南诏的时间、人物、使命等关键信息。从题记中可知,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袁滋以御史中丞身份,携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等,奉唐王之命前往云南册封蒙异牟寻为南诏。题记中还提到了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等人,以及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派的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等人,这些人物的出现展现了唐朝出使队伍的庞大与规格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唐朝与南诏之间复杂而重要的政治关系,为研究唐代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民族政策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唐袁滋摩崖石刻文字为隶书,书法刚劲秀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石刻所处的崖壁环境与书法相得益彰,增添了艺术魅力。与《资治通鉴》《新唐书》等后世编纂的史籍相比,摩崖石刻是事件亲历者在当时当地留下的第一手材料,未经后世史家的筛选与重构,具有特殊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唐袁滋摩崖石刻是唐朝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它记录了唐朝与南诏之间政治上的册封关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唐袁滋摩崖石刻见证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和解与合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唐袁滋摩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4]朱飞镝,袁滋题名摩崖与南诏归唐述略;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05-15.
[5]蒲骏,千年古道上的石刻档案——唐《袁滋题名摩崖》,云南档案,1995-02-15.
作者单位:昭通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讲好民族团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实践的昭通篇章”(SKPJ202472),项目负责人:马心明,审核人:李艳;昭通市2025年度(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昭通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学资源共享研究”(ZTZCKT2025114),项目负责人:马心明;昭通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Ztujk202552)等项目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乌蒙地区;五尺道;汉孟孝琚碑;唐袁滋摩崖
引言
2023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为我们进一步推广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服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行动指南和实践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的公共课程,通过对区域地方教学案例资源的挖掘与运用展开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课程建设提质增效。
乌蒙地区地处西南要冲,北连巴蜀,南接滇越,东通黔中,西达缅印,是巩固西南边疆、抵御外部侵扰的战略前沿。自秦开五尺道、汉筑西南夷道,西南地区开启了与中原地区频繁的互动,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名迹。
一、五尺道:交通动脉见证民族交融历程
盐津县五尺道是我国西南地区保存至今的古老道路,从秦朝开始修建,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不仅体现了古人修路架桥的聪明才智,更记录了中原和西南边疆各民族相互往来、共同发展的历史。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条条古道就像连接各地的纽带,把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交通古道始终是推动民族交融的重要纽带。
(一)秦代:边疆开拓与交通奠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威服四夷,君临天下”的政治抱负,将目光转向西南边疆。乌蒙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战略位置,使其成为秦朝拓展疆域的重要目标。李冰任蜀郡太守期间,就已开始修建修筑五尺道,秦统一六国后继续修筑。这条道路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起点,经豆沙关(今云南盐津),直抵滇池地区,因道路宽度仅约五尺,故得名“五尺道”。面对西南地区“山崖险峻”的恶劣地形,秦人采用“积薪烧岩”的方法,辅以人工开凿,在绝壁间硬生生开辟出这条战略通道。秦朝通过道路建设实现“置吏管理”,将西南边疆纳入国家行政体系。这种“道路-治所-移民”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有效强化了边疆对中央的政治认同。五尺道的建成,打破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长期存在的地理阻隔,更通过“诸此国颇置吏焉”的治理措施,将秦朝先进的郡县制首次推行至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统治的正式开始,使得中原文明与西南少数民族文明开始有了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五尺道正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西南边疆民族从分散走向联结的重要物证。它见证了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与融合的开端。
(二)汉唐时期:拓展与完善
汉代在秦代五尺道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拓展。汉武帝时期,唐蒙、司马相如先后主持西南夷道工程,将五尺道与夜郎道、灵关道相连,形成“北达巴蜀、南抵交趾”的交通网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西南夷道“商旅往来,日以千数”,中原的铁器、丝绸、漆器等手工业品经此南运,滇黔地区的筇竹、枸酱、马匹等特产也得以北输。这一时期五尺道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互动,中原的生产技术、文化观念不断传入西南,而西南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与物产也反向影响着中原,这种双向的交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注入了持续而强劲的动力。
(三)唐宋至明清:持续演变与文化积淀
唐宋时期,五尺道成为“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承载着中原与西南地区茶马互市的核心功能。宋代在今盐津设立“博易场”,专门管理茶叶、马匹贸易,这种经济互补性交换加速了区域市场整合。元代推行“站赤”制度,在五尺道沿线设立豆沙关站、乌蒙站等驿站,保障军政信息传递与商旅安全。明清时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大量汉族移民沿着五尺道涌入西南地区,形成了“汉夷杂居”的独特格局。在这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内涵不断丰富,五尺道沿线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贸易、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盐津县五尺道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各民族的交流史。这条在乌蒙山区的古道,从秦朝建成,到汉朝成为西南重要交通线,一直是连接中原和西南的关键通道。自开辟以来,它便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南边疆文明相互渗透的通道。在长期的贸易和生活中,各民族互相学习、彼此帮助,打破了地理的隔阂,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紧密关系。汉族移民带来儒家思想、农耕技术、建筑技艺,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歌舞、宗教信仰也反向影响中原。例如,彝族火把节习俗融入汉族节庆文化,汉族的四合院建筑在云南演变为“一颗印”民居。豆沙关古镇的关隘建筑融合了汉族城楼与彝族碉楼风格,寺庙内同时供奉孔子、观音与彝族毕摩神灵,生动展现了文化共生的独特魅力。这种文化的交融互鉴,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汉孟孝琚碑:见证乌蒙地区开发
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汉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达到鼎盛,具备了向边疆地区辐射影响力的雄厚实力。汉武帝为打通西南夷道,加强与西域及南亚的联系,进一步拓展帝国影响力,乌蒙地区成为汉朝经略西南的关键节点。乌蒙地区在汉代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带,其开发与治理不仅是汉朝巩固边疆、拓展疆域的战略举措,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与深化的历史缩影。汉孟孝琚碑作为汉代碑刻文化的珍贵遗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汉朝对乌蒙地区开发与治理的重要实物见证。
(一)偶然现世:开启了解汉朝乌蒙历史窗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深秋,云南昭通城南白泥井村的村民在修缮水沟时,意外掘出一方古朴的石碑。当时,昭通地区虽地处西南边陲,但也有不少关注地方历史文化的有识之士,他们对石碑的文字、形制进行初步探究,意识到其可能蕴含着关于本地古代历史的重要信息。消息传开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这块石碑,其古朴的形制与斑驳的文字,经学者鉴定为汉朝时期的碑文。汉孟孝琚碑的发现,为理解汉朝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手段推动乌蒙地区的开发进程,促进当地各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关键线索。
(二)石碑形制与碑文解读
汉孟孝琚碑碑额呈半圆形,浮雕着象征四方的“四灵”图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环绕着“孟孝琚碑”四个苍劲的篆书大字。碑身则以隶书阴刻着260余字的铭文,虽历经风雨侵蚀,仍可辨识出“十二随官未喻从师,少孺好学,才艺过人”等关键句段。从文字看,碑文书体处于篆隶过渡阶段,暗含文化适应 ——篆书是中原正统文字符号,隶书便于传播书写,这种字体融合,是汉文化与边疆文化对话的体现。叙事上,碑文记载的“十二随官未喻从师”,反映了汉朝在边疆推行儒学教育,儒家经典纳入当地教育体系,孝悌、仁义等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碑文引用“四知君子”和“六艺俱备”等儒家符号,“孝道神化”故事被记录,如孝悌、仁义等品德,反映了汉朝儒家思想在乌蒙地区的广泛传播。符号层的“四灵”浮雕,青龙白虎代表中原文化信仰,朱雀玄武融入西南地域崇拜,是汉越文化交叠设计的生动呈现。
碑文详细记载了东汉建初六年(公元81年),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不幸早逝,其妻(“犍为南安人也”,即今四川乐山人士)不远千里将其归葬祖茔的故事。而“归葬祖茔”则体现了中原宗法观念在乌蒙的扎根,强化了边疆民众对家族与国家的认同。碑文记述了孟孝琚的家族背景、成长经历以及他所具备的品德修养。从有限的文字中可知,孟孝琚出身于当地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家族,其成长过程中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推崇孝悌等道德准则。这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生命轨迹,更折射出当时乌蒙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在汉代大一统的背景下,儒家思想逐渐向边疆传播,孟孝琚的故事成为这种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融合的具体体现,也让我们透过个人命运看到整个时代的文化脉络与社会风尚。这块饱经沧桑的石碑,以其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与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研究汉代乌蒙地区历史沿革、民族交流融合以及丧葬文化习俗的关键实物证据。汉孟孝琚碑,它铭刻着汉朝经略边疆、推行行政建制的历史足迹,见证着中原与乌蒙地区经济互动、文化交流的生动图景,更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的珍贵记忆。这方石碑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由无数个体命运、民族交流故事编织而成的生动实践。
三、唐袁滋摩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千年印记
唐袁滋摩崖坐落于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山路西侧崖壁之上,处于盐津豆沙关“五尺道”的必经之处。豆沙关地势险要,两山壁立千仞,危石若悬,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和军事咽喉。这里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也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交流往来的关键节点。唐袁滋摩崖石刻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承载着唐朝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南地区密切联系的重要信息,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唐袁滋摩崖石刻的背景
唐朝时期,国力强盛,采取了较为开明的边疆政策。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在边疆地区推行羁縻政策。通过设立羁縻州府,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在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加强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唐朝与南诏的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演变过程。初唐时期,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一统洱海流域,双方关系友好。唐朝通过册封、贸易等方式与南诏保持着密切联系,南诏也积极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天宝年间,由于边将贪功冒进和政策失误,导致南诏叛唐归附吐蕃,双方爆发了“天宝战争”。唐军先后派兵二十万征讨,却遭致惨败,这场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深重灾难。此后,南诏在吐蕃的控制下,也深受其剥削压迫。到唐德宗时期,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国力大损,南诏也因战争和吐蕃的压迫处境艰难,双方都有了缓和关系的意愿。在此背景下,唐朝采纳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的战略,南诏王异牟寻也认识到“叛唐无益”,派使者三路赴唐表达归附之意,双方关系迎来转机。
唐贞元十年,御史中丞袁滋被任命为册南诏使,奉命赴滇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这一使命意义重大,标志着唐朝与南诏关系的重大转折,双方从此恢复和平友好交往。袁滋一行从长安出发,途经盐津豆沙关时,在路侧岩壁上刊石纪事,留下了袁滋题记摩崖石刻。重新册封南诏王,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映出唐与南诏友好关系的史实。此石刻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研究唐与南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唐袁滋摩崖石刻的内容与影响
唐袁滋摩崖石刻正文共12行,全文120余字,详细记录了袁滋出使南诏的时间、人物、使命等关键信息。从题记中可知,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袁滋以御史中丞身份,携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等,奉唐王之命前往云南册封蒙异牟寻为南诏。题记中还提到了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等人,以及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派的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等人,这些人物的出现展现了唐朝出使队伍的庞大与规格之高,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唐朝与南诏之间复杂而重要的政治关系,为研究唐代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民族政策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唐袁滋摩崖石刻文字为隶书,书法刚劲秀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石刻所处的崖壁环境与书法相得益彰,增添了艺术魅力。与《资治通鉴》《新唐书》等后世编纂的史籍相比,摩崖石刻是事件亲历者在当时当地留下的第一手材料,未经后世史家的筛选与重构,具有特殊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唐袁滋摩崖石刻是唐朝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它记录了唐朝与南诏之间政治上的册封关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唐袁滋摩崖石刻见证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和解与合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唐袁滋摩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
[4]朱飞镝,袁滋题名摩崖与南诏归唐述略;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05-15.
[5]蒲骏,千年古道上的石刻档案——唐《袁滋题名摩崖》,云南档案,1995-02-15.
作者单位:昭通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讲好民族团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实践的昭通篇章”(SKPJ202472),项目负责人:马心明,审核人:李艳;昭通市2025年度(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昭通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教学资源共享研究”(ZTZCKT2025114),项目负责人:马心明;昭通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Ztujk202552)等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