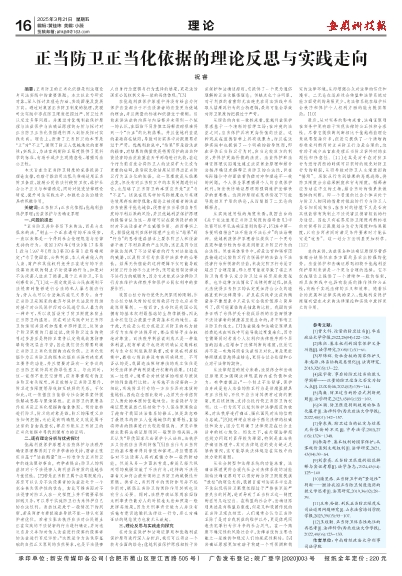发布日期:
正当防卫正当化依据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走向
文章字数:5179
摘要: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理论内涵、实践困境及发展方向。通过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梳理,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防卫限度把握过严、防卫过当认定过多等问题。并通过对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与法益保护与法确证原理的分析与探讨对正当防卫正当化依据进行深入剖析及探讨实践走向。理论上,澄清了正当防卫的本质是“正”对“不正”,强调了防卫人优越地位的重要性;实践上,为法官判断防卫限度提供了更科学的标准,有助于减少主观随意性,增强司法公正性。
本文旨在为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推动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正当防卫条款,鼓励公民依法行使防卫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同时对促进法律理论研究、提升司法实践水平、加强社会法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正当防卫;正当化依据;优越利益保护原理;法益保护与法确证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正当防卫并非书写下来的法,而是与生俱来的法。”制止一个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得到社会伦理规范与法律支持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第17条第1款与1997年《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如果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1]这一规定就是让公民在遇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进行合法的私人暴力救济行为,旁人也可以合法地实施见义勇为。由于正当防卫是国家的救济与保护无法及时到场时基于对公民保护而对公民进行私人暴力的一种许可,所以我国设定了防卫限度来防止正当防卫的滥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适用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宽泛,反而由于防卫限度的门槛过低,使得防卫过当的使用过多甚至是将防卫案件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情况层出不穷,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明确正当防卫正当化依据的内在价值。正当化依据作为正当防卫的根本依据应当具有决定成立要件的功能,并且需要对具有一定争议的正当防卫案件具有指导性意义。与此同时,这一依据不能凭空猜测,应当尊重现有的正当防卫有关规定,并且能够与正当防卫要件、防卫过当限度等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一依据应当能够为社会疑难案件提供解决思路与厘清路线。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是正当化根据的抽象体现。何时能够进行防卫,防卫的对象是谁,防卫的限度又应当如何把握,无论是有明确规定又或是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当能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中寻找到强有力的证明。
二、现有理论分析与优劣探讨
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与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确证原理都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前者主张应当基于“法益衡量”这一标准作为正当防卫中的违法阻却事由。有学者提出:防卫人的利益相对于不法侵害人的利益具有质的优越性与优位性。[2]若是正当防卫属于必要限度内,甚至可以认为不法侵害者的法益是处于一个完全丧失保护性的状态。由此可推当面对不法侵害时防卫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需要承担回避义务,可以勇于实施防卫行为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这是处于一般情况下的判断,若是两者有着极端差异就不能一律认定保护者优位。后者主张法秩序应当对公民制止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的行为进行确证,并对违反自身义务而对他人法益进行侵害的侵害者的法益进行否定评价。“这既是作为法秩序基础的自然正义原则的当然要求,也是不法侵害人自身行为逻辑与行为选择的结果,更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义务一致的具体体现。”[3]
在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中并没有给出为何保护法益相当于不法侵害者的法益更为优越的理由,并且衡量的标准和依据过于模糊。目前来讲法益的内容与内涵都并未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在面临不同价值立场解读时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比较结果。并且优越利益说的基础存在缺陷,导致司法实务中对限度要求过于严苛。优越利益说中,“结果”即是指法益的损害,对结果的衡量就是将所保护的法益和被侵害的法益放置在天平两端进行比较,在这个行为前首先会将防卫人的法益扩大化成为更重的砝码,最后取比较结果从而得出正当防卫行为正当化的依据。这一原理就是从结果出发,但没有对正当防卫中的本质问题进行讨论,也忽略了正当防卫的本质应当是“正”与“不正”。该说在现实中的实际效果也与其理论效果存在相悖现象:理论上被侵害者的法益应当被置于优先地位,侵害者应当承担自身引发的不利后果的风险,并且优越利益保护原理的提倡者认为这一原理可以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对不法侵害者产生威慑作用。然而事实上是,根据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产生的从“结果”到“行为”的思考进路基本上要求防卫人和侵害者平摊了不利后果的产生风险,这正是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不法侵害者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威胁,以及防卫行为在保护法益中的必要性。结果无价值论的这种逻辑不仅可能导致对防卫行为的不公正评价,还可能削弱法律对不法行为的威慑力,因为它未能充分诠释防卫行为在维护法律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公权力的行使受比例原则的限制,作为公权力缺失时的私权利救济行为也应当受此原则限制。一般而言,生命权是我国公民拥有的基本权利最基础的生物学根据,因此生命权往往会被置于最高基本权的地位。鉴于此,无论是公权力或是正当防卫的私力救济行为在维护法秩序时,都必须给予生命权绝对尊重。而法秩序利益说到底只是一种集体利益,现有学说中也没有明确认定集体权利与生命权到底孰轻孰重,或者说在利益权衡中,最核心利益并没有被明确规定。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违法阻却事由的成立往往是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权衡的结果。[4]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会对被侵害的利益与被保护的利益进行比较。与实施不法侵害的一方相比,实施防卫行为的一方应当具有本质的优越性,因此在全面比较时,必须充分考虑防卫人所处的本质的优越地位。法益保护与法确证愿意虽然已经相较于个人保全原理做出了趋向于我国法治体系的修正,但是其忽略了最根本的防卫人优越地位的重要性,直接将两者的损害进行比较是错误的。罗克辛教授主张将法确证原则同一般预防相关联,并且认为“即使国家无法保护个人法益,法秩序正义仍然应当得到伸张”[5]应当作为正当防卫的基本精神得到伸张和体现,并且需要具备对不法侵害人具有威慑力和一般预防功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若是已经无视刑罚的威慑实施了不法行为,这样的不法侵害者又如何会被所谓的正当防卫的威慑性所震慑。换言之,当刑罚中的预防作用并不起作用时,提倡正当防卫的预防作用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同时,法秩序确证原则在面临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时候也无法如预期一般发挥其效果,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并没有实施有意识地触犯法律这一行为,那么对确证法的规范效力也就无从谈起。
三、理论反思与实践走向探究
在对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则和优越利益保护原则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结论:优越利益保护原理相较于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则,它提供了一个更为通俗理解的正当化根据理论。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对于利益的看重即无法避免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从结果到行为的分析逻辑,最终可能会导致对防卫限度的把握过于严苛。
从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来看,优越利益保护原理基于一个清晰的哲学立场:在冲突的法益之间,应当保护具有更高价值的法益。这种观点在道德哲学上具有说服力,而且在法律实践中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即在评估正当防卫行为时,应当比较双方的利益,并保护更高价值的法益。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理试图通过建立法益保全原理和结合法秩序确证来解释正当防卫的合法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着价值对冲和理论不一致的问题。个人保全原理强调个人的自我保护权利,而法秩序确证原理则强调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性。这两种原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相互矛盾的结论,从而削弱了二元论的解释力。
从实践适用性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台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依稀可以寻见法确证原则的影子,[6]其中第一条便明确指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优越利益保护原理看似提供了一个更为直观和操作性的标准来判断正当防卫行为的合法性。但在具体案件中,若是法官和陪审团直接通过比较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与不法侵害行为所损害的法益,来决定防卫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那么很可能就导致了将正当防卫的案件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是故意犯罪。也许这种方法简化了法律判断过程,但是无法使得正当防卫的认定更加符合公众的道德直觉和法律期待。并且在实践中法益的衡量并不像想象中只是认定金钱价值那么简单明了,很可能面临的是抽象的比较。我国的实务证明了为保护处于较低层级的法益而损害不法侵害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并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7]法益保全和法确证原理虽然看起来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过度复杂化,因为它需要同时考虑个人权利和法律秩序两个层面的因素,这增加了法律判断的难度,但是它并不是一味地将两者法益相互对比,而是更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更符合社会伦理和公众对于法律的期待。
从法律规范的效力来看,法益保全和法确证原理更加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和效力。有学者提出:“一个制止不法侵害,保护自身或是他人法益的防卫行为是毋庸置疑具有正当性的,不仅不应当对其拥有过高的限制,更应该鼓励、支持公民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这一行为还可以起到维护法律规范的效果,对法秩序进行确证、强化国民对法的信赖与忠诚。”[8]这种观点有助于强化法律的权威性和效力,因为它明确了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相比之下,在处理法律规范效力问题时显得较为薄弱,特别是在法秩序确证原理中,其对法律规范的效力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可能导致法律规范在实践中的效力受到削弱。
从社会转型和法律系统的功能来看。法确证原理更符合现代社会对法律系统的功能期待法确证原则可以很好的为防卫限度提供“放松”的理论支持,我国目前司法实务中总是不免出现将防卫限度把握过于严格甚至是严重失当的问题,进而导致了正当防卫这一制度的适用几近空白。在转型的社会中,法确证原则虽然是向转型后靠拢,但是又和我国传统的正当防卫观点相近。人们通常会认为正当防卫除了是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以外,更是体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社会风气。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法律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维持和稳定人们的规范性期待。[9]法确证原理更加有助于构建一个可预测和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遵守。二元论在适应社会转型和法律系统功能方面受到的局限更少,为法律系统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能力提供帮助。[10]
最后,从对实务的影响来看,法确证原则在实务中更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尽管它提供的判断相比于优越利益理论来说要复杂许多,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标准来判断何时正当防卫行为是合理的,这有助于减少法官在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时的主观性和任意性。[11]尤其是对于在对防卫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避免对防卫行为的割裂,从而导致对防卫人主观意图的“揣测”。采取从行为到结果的思想进路,将防卫限度分为结果限度和行为限度。解释者应当站在中立的立场,结合当时的情景来做整体的判断。即一个普通的社会个体当处于与防卫人相同的情景时做出的行为与防卫人是否相同或相当,在当时的情境下又是否有其他能够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且损害较低的行为途径。因此只有在界定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时候将防卫限度划分为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只有当两者同时满足条件要素时才能认定是“过当”。这一划分方法明显更加科学。
[12]
总的来讲,法益保全和法确证原理尽管存在部分缺陷但在各方面均显示出较强的优势。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则相较于优越利益保护原则来讲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它不仅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清晰和一致的框架,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较高的操作性和公正性,有助于实现法律的正义和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深入,优越利益保护原理有望在未来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文科.论量的防卫过当[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04):122-136.
[2]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J].法学研究,2008(01):51-60.
[3]邓炜辉.论社会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起源、体系结构及类型化[J].法商研究,2015,32(05):13-22.
[4]段宇衡.事后的防卫过当的教义学阐释——以量的防卫过当之否定为切入点[J].江汉论坛,2024(03):139-144.
[5]高巍.防卫过当的阶层式判断规则[J].法学研究,2023,45(06):155-169.
[6]江溯.防卫限度判断规则的体系化展开[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01):142-157.
[7]劳东燕.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J].中外法学,2015,27(05):1324-1348.
[8]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J].法学研究,2021,43(04):39-54.
[9]刘崇亮.正当防卫限度的规范解释与实证考察[J].法学杂志,2024,45(04):125-140
[10]潘星丞.正当防卫中的“紧迫性”判断——激活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教义学思考[J].法商研究,2019,36(02):28-39.
[11]王玮,孙健.刑民正当防卫限度及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23,39(03):95-107.
[12]王政勋.正当防卫体系性地位的再思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06):123-133.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本文旨在为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推动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正当防卫条款,鼓励公民依法行使防卫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同时对促进法律理论研究、提升司法实践水平、加强社会法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正当防卫;正当化依据;优越利益保护原理;法益保护与法确证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正当防卫并非书写下来的法,而是与生俱来的法。”制止一个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得到社会伦理规范与法律支持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第17条第1款与1997年《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如果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1]这一规定就是让公民在遇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进行合法的私人暴力救济行为,旁人也可以合法地实施见义勇为。由于正当防卫是国家的救济与保护无法及时到场时基于对公民保护而对公民进行私人暴力的一种许可,所以我国设定了防卫限度来防止正当防卫的滥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适用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宽泛,反而由于防卫限度的门槛过低,使得防卫过当的使用过多甚至是将防卫案件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情况层出不穷,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明确正当防卫正当化依据的内在价值。正当化依据作为正当防卫的根本依据应当具有决定成立要件的功能,并且需要对具有一定争议的正当防卫案件具有指导性意义。与此同时,这一依据不能凭空猜测,应当尊重现有的正当防卫有关规定,并且能够与正当防卫要件、防卫过当限度等形成相互映照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一依据应当能够为社会疑难案件提供解决思路与厘清路线。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是正当化根据的抽象体现。何时能够进行防卫,防卫的对象是谁,防卫的限度又应当如何把握,无论是有明确规定又或是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当能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中寻找到强有力的证明。
二、现有理论分析与优劣探讨
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与法益保护与法秩序确证原理都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前者主张应当基于“法益衡量”这一标准作为正当防卫中的违法阻却事由。有学者提出:防卫人的利益相对于不法侵害人的利益具有质的优越性与优位性。[2]若是正当防卫属于必要限度内,甚至可以认为不法侵害者的法益是处于一个完全丧失保护性的状态。由此可推当面对不法侵害时防卫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需要承担回避义务,可以勇于实施防卫行为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这是处于一般情况下的判断,若是两者有着极端差异就不能一律认定保护者优位。后者主张法秩序应当对公民制止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的行为进行确证,并对违反自身义务而对他人法益进行侵害的侵害者的法益进行否定评价。“这既是作为法秩序基础的自然正义原则的当然要求,也是不法侵害人自身行为逻辑与行为选择的结果,更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义务一致的具体体现。”[3]
在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中并没有给出为何保护法益相当于不法侵害者的法益更为优越的理由,并且衡量的标准和依据过于模糊。目前来讲法益的内容与内涵都并未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在面临不同价值立场解读时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比较结果。并且优越利益说的基础存在缺陷,导致司法实务中对限度要求过于严苛。优越利益说中,“结果”即是指法益的损害,对结果的衡量就是将所保护的法益和被侵害的法益放置在天平两端进行比较,在这个行为前首先会将防卫人的法益扩大化成为更重的砝码,最后取比较结果从而得出正当防卫行为正当化的依据。这一原理就是从结果出发,但没有对正当防卫中的本质问题进行讨论,也忽略了正当防卫的本质应当是“正”与“不正”。该说在现实中的实际效果也与其理论效果存在相悖现象:理论上被侵害者的法益应当被置于优先地位,侵害者应当承担自身引发的不利后果的风险,并且优越利益保护原理的提倡者认为这一原理可以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对不法侵害者产生威慑作用。然而事实上是,根据优越利益保护原理产生的从“结果”到“行为”的思考进路基本上要求防卫人和侵害者平摊了不利后果的产生风险,这正是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不法侵害者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威胁,以及防卫行为在保护法益中的必要性。结果无价值论的这种逻辑不仅可能导致对防卫行为的不公正评价,还可能削弱法律对不法行为的威慑力,因为它未能充分诠释防卫行为在维护法律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公权力的行使受比例原则的限制,作为公权力缺失时的私权利救济行为也应当受此原则限制。一般而言,生命权是我国公民拥有的基本权利最基础的生物学根据,因此生命权往往会被置于最高基本权的地位。鉴于此,无论是公权力或是正当防卫的私力救济行为在维护法秩序时,都必须给予生命权绝对尊重。而法秩序利益说到底只是一种集体利益,现有学说中也没有明确认定集体权利与生命权到底孰轻孰重,或者说在利益权衡中,最核心利益并没有被明确规定。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违法阻却事由的成立往往是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权衡的结果。[4]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会对被侵害的利益与被保护的利益进行比较。与实施不法侵害的一方相比,实施防卫行为的一方应当具有本质的优越性,因此在全面比较时,必须充分考虑防卫人所处的本质的优越地位。法益保护与法确证愿意虽然已经相较于个人保全原理做出了趋向于我国法治体系的修正,但是其忽略了最根本的防卫人优越地位的重要性,直接将两者的损害进行比较是错误的。罗克辛教授主张将法确证原则同一般预防相关联,并且认为“即使国家无法保护个人法益,法秩序正义仍然应当得到伸张”[5]应当作为正当防卫的基本精神得到伸张和体现,并且需要具备对不法侵害人具有威慑力和一般预防功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若是已经无视刑罚的威慑实施了不法行为,这样的不法侵害者又如何会被所谓的正当防卫的威慑性所震慑。换言之,当刑罚中的预防作用并不起作用时,提倡正当防卫的预防作用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同时,法秩序确证原则在面临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时候也无法如预期一般发挥其效果,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并没有实施有意识地触犯法律这一行为,那么对确证法的规范效力也就无从谈起。
三、理论反思与实践走向探究
在对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则和优越利益保护原则进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结论:优越利益保护原理相较于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则,它提供了一个更为通俗理解的正当化根据理论。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对于利益的看重即无法避免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从结果到行为的分析逻辑,最终可能会导致对防卫限度的把握过于严苛。
从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来看,优越利益保护原理基于一个清晰的哲学立场:在冲突的法益之间,应当保护具有更高价值的法益。这种观点在道德哲学上具有说服力,而且在法律实践中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即在评估正当防卫行为时,应当比较双方的利益,并保护更高价值的法益。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理试图通过建立法益保全原理和结合法秩序确证来解释正当防卫的合法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着价值对冲和理论不一致的问题。个人保全原理强调个人的自我保护权利,而法秩序确证原理则强调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性。这两种原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相互矛盾的结论,从而削弱了二元论的解释力。
从实践适用性的角度来看,我国出台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依稀可以寻见法确证原则的影子,[6]其中第一条便明确指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优越利益保护原理看似提供了一个更为直观和操作性的标准来判断正当防卫行为的合法性。但在具体案件中,若是法官和陪审团直接通过比较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与不法侵害行为所损害的法益,来决定防卫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那么很可能就导致了将正当防卫的案件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是故意犯罪。也许这种方法简化了法律判断过程,但是无法使得正当防卫的认定更加符合公众的道德直觉和法律期待。并且在实践中法益的衡量并不像想象中只是认定金钱价值那么简单明了,很可能面临的是抽象的比较。我国的实务证明了为保护处于较低层级的法益而损害不法侵害者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并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7]法益保全和法确证原理虽然看起来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过度复杂化,因为它需要同时考虑个人权利和法律秩序两个层面的因素,这增加了法律判断的难度,但是它并不是一味地将两者法益相互对比,而是更能够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更符合社会伦理和公众对于法律的期待。
从法律规范的效力来看,法益保全和法确证原理更加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和效力。有学者提出:“一个制止不法侵害,保护自身或是他人法益的防卫行为是毋庸置疑具有正当性的,不仅不应当对其拥有过高的限制,更应该鼓励、支持公民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这一行为还可以起到维护法律规范的效果,对法秩序进行确证、强化国民对法的信赖与忠诚。”[8]这种观点有助于强化法律的权威性和效力,因为它明确了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相比之下,在处理法律规范效力问题时显得较为薄弱,特别是在法秩序确证原理中,其对法律规范的效力缺乏足够的重视,这可能导致法律规范在实践中的效力受到削弱。
从社会转型和法律系统的功能来看。法确证原理更符合现代社会对法律系统的功能期待法确证原则可以很好的为防卫限度提供“放松”的理论支持,我国目前司法实务中总是不免出现将防卫限度把握过于严格甚至是严重失当的问题,进而导致了正当防卫这一制度的适用几近空白。在转型的社会中,法确证原则虽然是向转型后靠拢,但是又和我国传统的正当防卫观点相近。人们通常会认为正当防卫除了是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以外,更是体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社会风气。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法律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维持和稳定人们的规范性期待。[9]法确证原理更加有助于构建一个可预测和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遵守。二元论在适应社会转型和法律系统功能方面受到的局限更少,为法律系统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的能力提供帮助。[10]
最后,从对实务的影响来看,法确证原则在实务中更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尽管它提供的判断相比于优越利益理论来说要复杂许多,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标准来判断何时正当防卫行为是合理的,这有助于减少法官在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时的主观性和任意性。[11]尤其是对于在对防卫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可以很好的避免对防卫行为的割裂,从而导致对防卫人主观意图的“揣测”。采取从行为到结果的思想进路,将防卫限度分为结果限度和行为限度。解释者应当站在中立的立场,结合当时的情景来做整体的判断。即一个普通的社会个体当处于与防卫人相同的情景时做出的行为与防卫人是否相同或相当,在当时的情境下又是否有其他能够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且损害较低的行为途径。因此只有在界定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时候将防卫限度划分为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只有当两者同时满足条件要素时才能认定是“过当”。这一划分方法明显更加科学。
[12]
总的来讲,法益保全和法确证原理尽管存在部分缺陷但在各方面均显示出较强的优势。法益保护和法确证原则相较于优越利益保护原则来讲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它不仅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清晰和一致的框架,而且在实践中也具有较高的操作性和公正性,有助于实现法律的正义和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深入,优越利益保护原理有望在未来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文科.论量的防卫过当[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04):122-136.
[2]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J].法学研究,2008(01):51-60.
[3]邓炜辉.论社会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起源、体系结构及类型化[J].法商研究,2015,32(05):13-22.
[4]段宇衡.事后的防卫过当的教义学阐释——以量的防卫过当之否定为切入点[J].江汉论坛,2024(03):139-144.
[5]高巍.防卫过当的阶层式判断规则[J].法学研究,2023,45(06):155-169.
[6]江溯.防卫限度判断规则的体系化展开[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01):142-157.
[7]劳东燕.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J].中外法学,2015,27(05):1324-1348.
[8]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J].法学研究,2021,43(04):39-54.
[9]刘崇亮.正当防卫限度的规范解释与实证考察[J].法学杂志,2024,45(04):125-140
[10]潘星丞.正当防卫中的“紧迫性”判断——激活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教义学思考[J].法商研究,2019,36(02):28-39.
[11]王玮,孙健.刑民正当防卫限度及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2023,39(03):95-107.
[12]王政勋.正当防卫体系性地位的再思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06):123-133.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