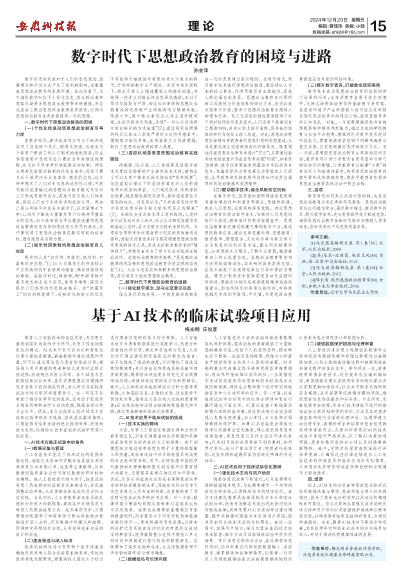发布日期:
数字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进路
文章字数:2651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重塑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环境。在此背景下,本文剖析数字时代下个性化信息、娱乐性因素和虚拟化场景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进路,以期为思想政治教育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一、数字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一)个性化信息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度
在数字时代,算法技术的应用与不断改进实现了信息的个性化、精准化投递,这确实为个体用户提供了私人订制式的适配服务,但也容易使用户忽视信息以需求为导向推送的逻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智能算法的控制。网民长期身处由算法控制的信息茧房中,逐渐习惯且乐于接受迎合自身喜好、需求的信息,这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性心理,可能导致传统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无法对人们形成有效吸引力,甚至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降低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再加上部分网络平台在资本驱动下,以流量增长为中心,向用户推送大量激发用户兴趣却质量低劣的信息,而不能有效为平台提供流量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的推送则无法得到保证,这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领域的话语权,进而削弱其引导力度。
(二)娱乐性因素制约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效度
现实的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1]人作为感性化的存在物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能够调动感官、调动情感情绪的事物。在数字时代,随着VR、MR和XR等新兴数字技术的生成与应用,能够多维度、深层次娱乐人们感官的信息越来越多。在“流量至上”的目的性逻辑下,这些新兴的娱乐性信息因其能够大幅度掠夺有限的受众注意力的特质,开始席卷数字生产领域。在资本运作逻辑下,娱乐元素无止境地攫取人的感性欲望,并使得一些受众对娱乐性信息形成瘾欲,而对于那些风格较为严肃、形式相对单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则很难产生情感共鸣与情绪共振。除此之外,娱乐性元素还会入侵主流价值领域,生成泛娱乐化现象,会使“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2],通过将荒诞滑稽的娱乐元素注入崇高严肃的主流符号意象中,模糊意识形态界限,淡漠集体主义价值逻辑,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度。
(三)虚拟化场景悬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属性
传感器、5G互联、人工智能等底层数字技术为虚拟化场景的产生提供技术支持,建构出了可以为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的“世外桃源”,但在虚拟幻境之下的是智能算法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欲望的掌控。人们越是沉浸、依赖虚拟化场景,越是想逃离现实世界,最终造成虚拟与现实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科技无论发达到什么地步,社会生活都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进行,是无法用任何技术来替代的。当虚拟世界带来的快感凌驾于现实世界的物质内容时,虚拟化场景技术将不再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技术工具,而成为控制受教育者的“精神鸦片”,受教育者失去了参与社会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实效性”[4]。无法与现实实践相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空洞且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数字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路
(一)强化数字理念,坚守主流意识形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在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保障受教育者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者还要明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坚持以技术服务于价值,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私人化信息的推送容易使用户处于相对封闭的信息系统中,人们逐渐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造成认知上的片面性,容易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误入歧途。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尤其是要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既要通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来进行“守正”,又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创新”,如采用3D视效、数字仿真等技术将蕴涵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物宝藏生动复现在人们面前,让受教育者在极致的视觉体验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二)联动数字技术,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在数字时代,低质量的虚假网络信息凭借其富有煽动性和刺激性等特点,传播性较强,扰乱人们思想,引发网络舆情危机。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联动数字技术,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指引与规范,将舆情风险扼杀在摇篮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通过搭建可靠的数字平台,集成网民数据信息,建设完善党建引领、思想教育、教育教学、管理服务、文化娱乐等与群众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系统,整合网民数据信息,分析预测大众需求,了解大众意愿,提供健康向上的正能量信息。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实时研判舆情发展态势,在技术赋能下实现网络舆论引导和管控全覆盖。要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实现自动化监测网络舆情,借助区块链信息核查机制精准追查舆情源头,形成网格化的舆情风险防控,对舆情危机力争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安全可控的网络环境。
(三)提升数字素养,打破虚拟现实隔阂
数字技术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新的学习场景的同时,也将受教育者置于技术环境中,沉浸式场景体验使得价值渗透不易觉察,在虚拟环境中产生的虚拟人格可能会压制甚至替代现实世界中的现实人格,造成受教育者的认知混乱。对此,一方面要增强受教育者的逻辑思维和理性判断能力,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平台教育,增强网民对数字技术规训的抵抗力,摆脱情绪欲望控制下的精神麻痹与意志涣散,自觉抵制庸俗低质的娱乐文化。另一方面,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教育者可以设计受教育者更易感知与学习理论知识的情境,让受教育者以叙事“主角”的身份代入到叙事内容中,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所要传达的情感态度,激发受教育者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主动性。
三、结语
数字时代的到来已然是大势所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的现实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应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数字理念、联动数字技术、提升数字素养,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优势,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做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时代洪流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郝文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数字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一)个性化信息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度
在数字时代,算法技术的应用与不断改进实现了信息的个性化、精准化投递,这确实为个体用户提供了私人订制式的适配服务,但也容易使用户忽视信息以需求为导向推送的逻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智能算法的控制。网民长期身处由算法控制的信息茧房中,逐渐习惯且乐于接受迎合自身喜好、需求的信息,这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性心理,可能导致传统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无法对人们形成有效吸引力,甚至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降低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再加上部分网络平台在资本驱动下,以流量增长为中心,向用户推送大量激发用户兴趣却质量低劣的信息,而不能有效为平台提供流量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的推送则无法得到保证,这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领域的话语权,进而削弱其引导力度。
(二)娱乐性因素制约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效度
现实的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1]人作为感性化的存在物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能够调动感官、调动情感情绪的事物。在数字时代,随着VR、MR和XR等新兴数字技术的生成与应用,能够多维度、深层次娱乐人们感官的信息越来越多。在“流量至上”的目的性逻辑下,这些新兴的娱乐性信息因其能够大幅度掠夺有限的受众注意力的特质,开始席卷数字生产领域。在资本运作逻辑下,娱乐元素无止境地攫取人的感性欲望,并使得一些受众对娱乐性信息形成瘾欲,而对于那些风格较为严肃、形式相对单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则很难产生情感共鸣与情绪共振。除此之外,娱乐性元素还会入侵主流价值领域,生成泛娱乐化现象,会使“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2],通过将荒诞滑稽的娱乐元素注入崇高严肃的主流符号意象中,模糊意识形态界限,淡漠集体主义价值逻辑,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度。
(三)虚拟化场景悬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属性
传感器、5G互联、人工智能等底层数字技术为虚拟化场景的产生提供技术支持,建构出了可以为用户带来沉浸式体验的“世外桃源”,但在虚拟幻境之下的是智能算法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欲望的掌控。人们越是沉浸、依赖虚拟化场景,越是想逃离现实世界,最终造成虚拟与现实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科技无论发达到什么地步,社会生活都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进行,是无法用任何技术来替代的。当虚拟世界带来的快感凌驾于现实世界的物质内容时,虚拟化场景技术将不再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技术工具,而成为控制受教育者的“精神鸦片”,受教育者失去了参与社会实践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实效性”[4]。无法与现实实践相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空洞且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数字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路
(一)强化数字理念,坚守主流意识形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在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保障受教育者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者还要明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坚持以技术服务于价值,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私人化信息的推送容易使用户处于相对封闭的信息系统中,人们逐渐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造成认知上的片面性,容易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误入歧途。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尤其是要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既要通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来进行“守正”,又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意识形态宣传来实现“创新”,如采用3D视效、数字仿真等技术将蕴涵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物宝藏生动复现在人们面前,让受教育者在极致的视觉体验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二)联动数字技术,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在数字时代,低质量的虚假网络信息凭借其富有煽动性和刺激性等特点,传播性较强,扰乱人们思想,引发网络舆情危机。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联动数字技术,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指引与规范,将舆情风险扼杀在摇篮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通过搭建可靠的数字平台,集成网民数据信息,建设完善党建引领、思想教育、教育教学、管理服务、文化娱乐等与群众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系统,整合网民数据信息,分析预测大众需求,了解大众意愿,提供健康向上的正能量信息。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实时研判舆情发展态势,在技术赋能下实现网络舆论引导和管控全覆盖。要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实现自动化监测网络舆情,借助区块链信息核查机制精准追查舆情源头,形成网格化的舆情风险防控,对舆情危机力争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安全可控的网络环境。
(三)提升数字素养,打破虚拟现实隔阂
数字技术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创设新的学习场景的同时,也将受教育者置于技术环境中,沉浸式场景体验使得价值渗透不易觉察,在虚拟环境中产生的虚拟人格可能会压制甚至替代现实世界中的现实人格,造成受教育者的认知混乱。对此,一方面要增强受教育者的逻辑思维和理性判断能力,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与社会平台教育,增强网民对数字技术规训的抵抗力,摆脱情绪欲望控制下的精神麻痹与意志涣散,自觉抵制庸俗低质的娱乐文化。另一方面,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教育者可以设计受教育者更易感知与学习理论知识的情境,让受教育者以叙事“主角”的身份代入到叙事内容中,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所要传达的情感态度,激发受教育者在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主动性。
三、结语
数字时代的到来已然是大势所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的现实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应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数字理念、联动数字技术、提升数字素养,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优势,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做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时代洪流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郝文清.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