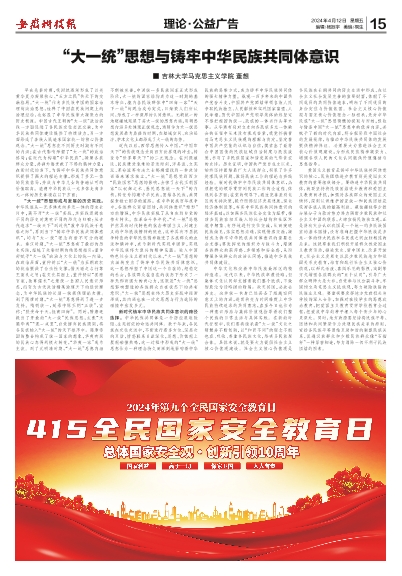发布日期:
“大一统”思想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章字数:3247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大一统”作为多民族中国的国家治理的政治思想,诠释了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治理经验,也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历史根源。中国古代王朝的“大一统”政治实践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形成了各族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大一统”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古代影响形塑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近代为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各族群众力量,共御外侮贡献了不竭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的当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并成为中华儿女的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追溯中华民族从一元多体走向多元一体的历史体现在以下方面:
“大一统”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从一元多体走向多元一体的历史长河中,离不开“大一统”实践,其实践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式与归宿:从古代追求“一统天下”到近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再到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与“大一统”理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有了最初的历史实践,超越了先秦时期的纯思想指引:董仲舒赋予“大一统”政治与文化上的统一内涵。在政治层面,董仲舒以“大一统”为王朝政权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借天道之名行尊王重礼之用;在文化层面上,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统一全国人民意识形态,衍变为古代政治精英治理天下的经世理念,为中华民族的长期一统提供理论支撑。到了隋唐时期,“大一统”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隋朝统一,延承中原王朝“正统”,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同时,隋唐还提出了开放的“大一统”民族思想,主张“无隔华夷”“混一戎夏”,自觉摒弃民族隔阂,将各民族纳入“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中。隋唐帝国的整合构成了统一国家的想象,华夷有别的民族心态得到极大转变,“华夷一家”成为主流。到了元明清时期,“大一统”思想内涵不断被完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阶段,大一统的国家结构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境内各民族群体中“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观念成为定式,日渐被人们所认同,形成了一种深厚的认同意识。元朝统一的地理疆域延展了其大一统的思想内涵,明朝思想内涵多处体现正统观念,清朝作为大一统思想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在疆域空间、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上都形成了大一统的态势。
近代以后,西学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即天下”的传统观念受到西方世界观的冲击,转变为“世界即天下”的二元观念。在列强殖民、民族遭受危难的紧迫时刻,洋务派、立宪派、革命派等有志之士都期望找到一种政治话语来谋求独立,“大一统”思想受到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去掉了古代王朝国家“以权御之术、愚民思想统一天下”的内核,转变为构建中华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中华民族百年抗争中,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共同体意识“雏形”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化。在革命斗争年代,“大一统”思想俨然具有时代特色的抗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色,这种具有不屈抗争特色的中华民族精神融进了各族群众的血液和精神中,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底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大一统”思想的内涵转变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思想形塑了中国这一个自在的、超稳定的社会,各族群众在自在的状态下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影响塑造的各族群众自在状态下的共有意识。“大一统”思想在伟大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其内涵也在一次次思想与行为选择的碰撞中愈发多元。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经艰难险阻、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数千年来,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多方位、深层次的互动,情感联系日益深化,思想、价值观上屡现碰撞共鸣,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始终坚定不移把祖国的统一、民族的一体当作头等大事。从华夷有别对立走向各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征程中从来没有现成答案,我党怀揣着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解与肯定,坚定着中国共产党能的认识与自信,摸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政策,书写了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的气势恢宏的史诗。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许多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各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提升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以加强各民族社会交往为纽带,推动各民族在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频繁、有序地进行交往交流,从而突破民族偏见,落实思想沟通,实现情感交融,凝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支撑;要发挥党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增强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率遭侵略,但集体文化认同却支撑着我们整个民族,不致彻底沦为侵略国的附属。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种统一本身已经具备了超越空间意义上的内涵,进而转变为时间维度上中华民族持续追求的共同意志,直至今日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集体价值观指导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与具体实践。在新的时代征程中,我们要持续承袭“大一统”文化之精髓并不断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包容、吸收、尊重各民族文化,形成多民族聚合体。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的历史生活中形成、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完善的重要财富,体现了不同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明晰了不同成员的身份定位与价值依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核心价值理念一脉相承,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精髓的提取与归纳,吸收与借鉴中国“大一统”思想中的优秀内容,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精神保证。必须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形成民族精神凝聚力、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提供价值遵循与思想指导。
爱国主义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坚持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两手抓,加强对各族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刻认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藏独疆独等少数分裂分子与敌对势力竭力隔断少数民族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联系,大肆宣扬民族独立观,正是没有充分认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和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推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少数民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式活泼、喜闻乐见的影视、戏剧等方式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广大群众明辨大是大非,自觉参与反分裂斗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努力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要重视要发挥地方党政机关与学校的深入合作,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同时,地方政府要坚持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宣扬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汉族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相连,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
“大一统”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华民族从一元多体走向多元一体的历史长河中,离不开“大一统”实践,其实践逻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式与归宿:从古代追求“一统天下”到近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再到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与“大一统”理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有了最初的历史实践,超越了先秦时期的纯思想指引:董仲舒赋予“大一统”政治与文化上的统一内涵。在政治层面,董仲舒以“大一统”为王朝政权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借天道之名行尊王重礼之用;在文化层面上,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统一全国人民意识形态,衍变为古代政治精英治理天下的经世理念,为中华民族的长期一统提供理论支撑。到了隋唐时期,“大一统”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隋朝统一,延承中原王朝“正统”,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同时,隋唐还提出了开放的“大一统”民族思想,主张“无隔华夷”“混一戎夏”,自觉摒弃民族隔阂,将各民族纳入“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中。隋唐帝国的整合构成了统一国家的想象,华夷有别的民族心态得到极大转变,“华夷一家”成为主流。到了元明清时期,“大一统”思想内涵不断被完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阶段,大一统的国家结构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境内各民族群体中“四海一家”“天下一统”的观念成为定式,日渐被人们所认同,形成了一种深厚的认同意识。元朝统一的地理疆域延展了其大一统的思想内涵,明朝思想内涵多处体现正统观念,清朝作为大一统思想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在疆域空间、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上都形成了大一统的态势。
近代以后,西学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即天下”的传统观念受到西方世界观的冲击,转变为“世界即天下”的二元观念。在列强殖民、民族遭受危难的紧迫时刻,洋务派、立宪派、革命派等有志之士都期望找到一种政治话语来谋求独立,“大一统”思想受到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去掉了古代王朝国家“以权御之术、愚民思想统一天下”的内核,转变为构建中华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中华民族百年抗争中,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共同体意识“雏形”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化。在革命斗争年代,“大一统”思想俨然具有时代特色的抗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色,这种具有不屈抗争特色的中华民族精神融进了各族群众的血液和精神中,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底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大一统”思想的内涵转变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思想形塑了中国这一个自在的、超稳定的社会,各族群众在自在的状态下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这就是“大一统”思想影响塑造的各族群众自在状态下的共有意识。“大一统”思想在伟大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其内涵也在一次次思想与行为选择的碰撞中愈发多元。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经艰难险阻、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数千年来,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多方位、深层次的互动,情感联系日益深化,思想、价值观上屡现碰撞共鸣,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始终坚定不移把祖国的统一、民族的一体当作头等大事。从华夷有别对立走向各民族多元一体融合的征程中从来没有现成答案,我党怀揣着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理解与肯定,坚定着中国共产党能的认识与自信,摸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政策,书写了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的气势恢宏的史诗。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许多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各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提升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以加强各民族社会交往为纽带,推动各民族在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频繁、有序地进行交往交流,从而突破民族偏见,落实思想沟通,实现情感交融,凝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支撑;要发挥党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增强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率遭侵略,但集体文化认同却支撑着我们整个民族,不致彻底沦为侵略国的附属。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种统一本身已经具备了超越空间意义上的内涵,进而转变为时间维度上中华民族持续追求的共同意志,直至今日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集体价值观指导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与具体实践。在新的时代征程中,我们要持续承袭“大一统”文化之精髓并不断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包容、吸收、尊重各民族文化,形成多民族聚合体。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的历史生活中形成、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完善的重要财富,体现了不同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明晰了不同成员的身份定位与价值依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核心价值理念一脉相承,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精髓的提取与归纳,吸收与借鉴中国“大一统”思想中的优秀内容,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精神保证。必须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形成民族精神凝聚力、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提供价值遵循与思想指导。
爱国主义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坚持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两手抓,加强对各族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刻认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藏独疆独等少数分裂分子与敌对势力竭力隔断少数民族和社会主义中国的联系,大肆宣扬民族独立观,正是没有充分认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和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推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少数民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式活泼、喜闻乐见的影视、戏剧等方式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广大群众明辨大是大非,自觉参与反分裂斗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努力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观。要重视要发挥地方党政机关与学校的深入合作,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同时,地方政府要坚持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宣扬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汉族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相连,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