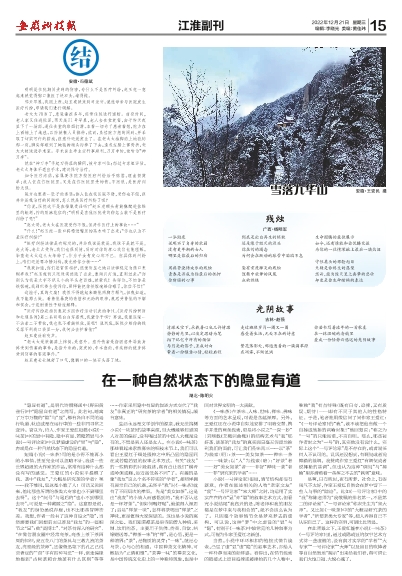发布日期:
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隐显有道
文章字数:2081
湖北·陈明火
“隐显有道”,是明代诗僧释函中《野田黄雀行》中“隐显自有道”之简写。此名句,暗寓了万事万物的“隐”与“显”,都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轨道、轨迹或是在运行中的一些非同寻常之变异。窃以为,诗人、作家王爱红短篇小说《一味茶》中的显中有隐、隐中有显、若隐若显与小说《一号评论家》中以梦境虚设的“显”与“隐”,亦或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隐显有道。
短篇小说《一味茶》写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情,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读一些世界超级的大作家的作品,常常有这种什么都没有写的感觉。王爱红的小说似乎提醒了我。茶中“我友”,“大概是研究茶的学者?嘿——我不能说,您这是小瞧了人!可话又说回来,他比那些所谓的茶类大专家也小不到哪里去呀”。这个“问号”与尾后的“也小不到哪里去呀”,可说是一种藏匿之“隐”。这意思是说,“我友”的身份虽说存疑,也不比那些冒牌货差。我想,作者一经有了这种自设之“隐”,当然需要我们回想前面已涉及“我友”的一些细节之“显”:他“是博士”、“对茶有深入的研究”、“在微信朋友圈中经常亮茶,亮茶上茶下茶四周的知识,亮五花八门的茶具与三教九流的茶友,亮高级的茶师”,还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剑走偏锋地提到“古树茶和台地茶有什么区别”等等……作家采用隐中有显的叙述方式交代了“我友”非真正的“研究茶的学者”的相关情况,颇有意味。
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无法揣测小说《一味茶》的故事来源,但大概能够知道国人对茶的偏好,没有喝过茶的中国人大概是没有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小说《一味茶》那些看起来索然寡味的细枝末节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爱红于细处摄神之中所凸显的隐显同在或若隐若显的叙事艺术方式。有关“我友”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叙述,真有点让我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了。有趣的是像“我友”这么个名不符实的“学者”,却照样拥有展示自己的机遇,无怪乎“我”对《一味茶》就有了不同层次的禅悟。先是“美女如茶”,这是由“我友”的小情人而感悟到的,“我不否认这是一杯好茶”,“但如何喝好呢”,就值得人深思了;后是“禅茶一味”,怎样将茶喝出“禅茶”之禅味,更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这也是小说的寓深之处。我们知道禅茶是指寺院僧人种植、采制、饮用的茶。主要用于供佛、待客、自饮、结缘赠送等。“禅茶一味”的“禅”,是心悟,更是一种境界;“茶”,是物质的灵芽;“一味”,就是心与茶、心与心的相通。中国禅茶文化精神,可概括为“正清和雅”。“茶禅一味”的禅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一味茶》在茶味、人味、世味、禅味、佛味等方面的艺术呈现,可说是含蕴深厚。另外,王爱红还在小说中自如地安排了明暗交替、携手并进的两条线索,更是将小说之“一深一妙”(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结构艺术与“我”那好茶、谈茶的“我友”的真实面目毫无保留地推到我们的面前,可让我们品味再三——以“茶”为线索(明):茶——美女如茶——禅味一茶——一味茶;以“人”为线索(暗):“好茶”者——好“美女如茶”者——非好“禅味一茶”者——非“研究茶的学者”……
小说《一号评论家》很短,情节结构却很有新意。作者在叙述相关的人物“老家文友”“我”“一号评论家”“宋大师”之时,均运用了实实在在的亦“显”亦“隐”的叙事艺术方式,但看完小说结尾“我高兴的是,陈老师和我的朋友都是在梦中来与我相会的”,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只因整个故事情节全是梦来梦去的虚构。可以说,这种“梦”中之虚设的“显”与“隐”,有别于《一味茶》中较常见的几种叙事方式,可视为作家王爱红之新创。
当然,小说中环环相扣的链接式情节线索,凸显了虚“显”虚“隐”的叙事艺术,亦给人一种朴鼻而来的新鲜感。看得出,在情节线索的链接式上盲目追捧或被捧抬的几个人物中,唯独“我”有点特殊(既有自夸、追捧,又有质疑、期待)——即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性格特征。于是,笔者就用微信问了问作家王爱红:“《一号评论家》的“我”,该不该把他当做一个自捧或他捧的讽喻对象?”他回复说:“称之为“一号”的只能是谁,不言自明。那么,那些被作者封之为“一号”的,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实际上这个“一号评论家”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任何人不认可的。讥讽还没想到,有调侃或者说揶揄的基调。我赞成作家王爱红“有调侃或者说揶揄的基调”,但也认为这种“调侃”与“揶揄”里亦潜蕴着一些挥之不去的“讽刺”意味。
是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社会上,有些风气不太好,作家王爱红自然会在梦中留下一些人与事的“踪迹”。比如《一号评论家》中的“我”称陈老师为“我敬佩的排名第一,不是第二的评论家”、“一号评论家”称宋先生为“宋大师”。又比如《一味茶》中的“大概是研究茶的学者”、“所谓茶类大专家”等,把人弄得自己不认识自己了。这样的实例,可谓比比皆是。
在此背景之下,王爱红能在小说《一味茶》《一号评论家》里,通过或隐或显的叙事艺术方式将一些虚假的、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大专家”“一号评论家”“大师”以及盲目的吹捧者等自自然然地“揭示”出来给我们看,真可谓让我们大饱口福、大悦心魂了。
“隐显有道”,是明代诗僧释函中《野田黄雀行》中“隐显自有道”之简写。此名句,暗寓了万事万物的“隐”与“显”,都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轨道、轨迹或是在运行中的一些非同寻常之变异。窃以为,诗人、作家王爱红短篇小说《一味茶》中的显中有隐、隐中有显、若隐若显与小说《一号评论家》中以梦境虚设的“显”与“隐”,亦或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隐显有道。
短篇小说《一味茶》写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情,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读一些世界超级的大作家的作品,常常有这种什么都没有写的感觉。王爱红的小说似乎提醒了我。茶中“我友”,“大概是研究茶的学者?嘿——我不能说,您这是小瞧了人!可话又说回来,他比那些所谓的茶类大专家也小不到哪里去呀”。这个“问号”与尾后的“也小不到哪里去呀”,可说是一种藏匿之“隐”。这意思是说,“我友”的身份虽说存疑,也不比那些冒牌货差。我想,作者一经有了这种自设之“隐”,当然需要我们回想前面已涉及“我友”的一些细节之“显”:他“是博士”、“对茶有深入的研究”、“在微信朋友圈中经常亮茶,亮茶上茶下茶四周的知识,亮五花八门的茶具与三教九流的茶友,亮高级的茶师”,还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剑走偏锋地提到“古树茶和台地茶有什么区别”等等……作家采用隐中有显的叙述方式交代了“我友”非真正的“研究茶的学者”的相关情况,颇有意味。
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无法揣测小说《一味茶》的故事来源,但大概能够知道国人对茶的偏好,没有喝过茶的中国人大概是没有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小说《一味茶》那些看起来索然寡味的细枝末节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爱红于细处摄神之中所凸显的隐显同在或若隐若显的叙事艺术方式。有关“我友”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叙述,真有点让我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了。有趣的是像“我友”这么个名不符实的“学者”,却照样拥有展示自己的机遇,无怪乎“我”对《一味茶》就有了不同层次的禅悟。先是“美女如茶”,这是由“我友”的小情人而感悟到的,“我不否认这是一杯好茶”,“但如何喝好呢”,就值得人深思了;后是“禅茶一味”,怎样将茶喝出“禅茶”之禅味,更是值得大家深思的。这也是小说的寓深之处。我们知道禅茶是指寺院僧人种植、采制、饮用的茶。主要用于供佛、待客、自饮、结缘赠送等。“禅茶一味”的“禅”,是心悟,更是一种境界;“茶”,是物质的灵芽;“一味”,就是心与茶、心与心的相通。中国禅茶文化精神,可概括为“正清和雅”。“茶禅一味”的禅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一味茶》在茶味、人味、世味、禅味、佛味等方面的艺术呈现,可说是含蕴深厚。另外,王爱红还在小说中自如地安排了明暗交替、携手并进的两条线索,更是将小说之“一深一妙”(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结构艺术与“我”那好茶、谈茶的“我友”的真实面目毫无保留地推到我们的面前,可让我们品味再三——以“茶”为线索(明):茶——美女如茶——禅味一茶——一味茶;以“人”为线索(暗):“好茶”者——好“美女如茶”者——非好“禅味一茶”者——非“研究茶的学者”……
小说《一号评论家》很短,情节结构却很有新意。作者在叙述相关的人物“老家文友”“我”“一号评论家”“宋大师”之时,均运用了实实在在的亦“显”亦“隐”的叙事艺术方式,但看完小说结尾“我高兴的是,陈老师和我的朋友都是在梦中来与我相会的”,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只因整个故事情节全是梦来梦去的虚构。可以说,这种“梦”中之虚设的“显”与“隐”,有别于《一味茶》中较常见的几种叙事方式,可视为作家王爱红之新创。
当然,小说中环环相扣的链接式情节线索,凸显了虚“显”虚“隐”的叙事艺术,亦给人一种朴鼻而来的新鲜感。看得出,在情节线索的链接式上盲目追捧或被捧抬的几个人物中,唯独“我”有点特殊(既有自夸、追捧,又有质疑、期待)——即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性格特征。于是,笔者就用微信问了问作家王爱红:“《一号评论家》的“我”,该不该把他当做一个自捧或他捧的讽喻对象?”他回复说:“称之为“一号”的只能是谁,不言自明。那么,那些被作者封之为“一号”的,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实际上这个“一号评论家”是不存在的,或者说任何人不认可的。讥讽还没想到,有调侃或者说揶揄的基调。我赞成作家王爱红“有调侃或者说揶揄的基调”,但也认为这种“调侃”与“揶揄”里亦潜蕴着一些挥之不去的“讽刺”意味。
是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社会上,有些风气不太好,作家王爱红自然会在梦中留下一些人与事的“踪迹”。比如《一号评论家》中的“我”称陈老师为“我敬佩的排名第一,不是第二的评论家”、“一号评论家”称宋先生为“宋大师”。又比如《一味茶》中的“大概是研究茶的学者”、“所谓茶类大专家”等,把人弄得自己不认识自己了。这样的实例,可谓比比皆是。
在此背景之下,王爱红能在小说《一味茶》《一号评论家》里,通过或隐或显的叙事艺术方式将一些虚假的、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大专家”“一号评论家”“大师”以及盲目的吹捧者等自自然然地“揭示”出来给我们看,真可谓让我们大饱口福、大悦心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