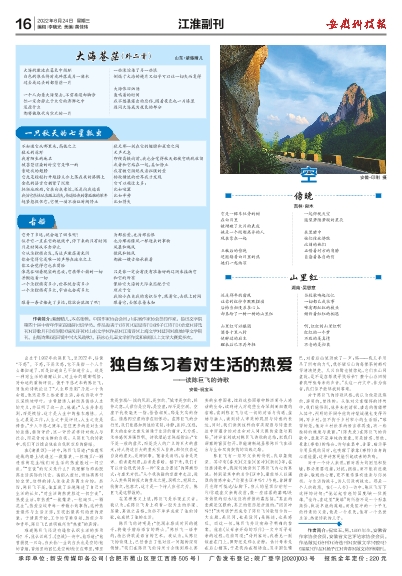发布日期:
独自练习着对生活的热爱
文章字数:2249
安徽·祝宝玉
出生于1982年的陈巨飞,至2022年,恰值“不惑”。不惑,不是无惑,它不是指一个人什么都知道了,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清醒认知,对生命的醍醐领悟,对命运的重新评议。值于不惑之年的陈巨飞,用他的诗歌论证了“人生即悲剧”乃是一个伪命题,他还是那么热爱着生活,并在诗歌中予以深情地呼吁。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给人生的定义,亦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人生并非悲剧,而是懊恼,这才是人生中的基本感情。人生之晨是工作,人生之午是评议,人生之夜是祷告。”步入不惑之庚年,往往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总结,继而评价,这一评价并非针对他人与社会,而是针对主体的自我。从陈巨飞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在自我跃空后的俯瞰。
在《清晨颂》一诗中,陈巨飞写道:“在蔬菜进城的路上/我遇见一截蕹菜、一粒豌豆/一颗遗落的花生/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空谈”的定义是什么?我理解为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议论。高蹈入虚幻,而远离真切的尘世,这样的诗人往往是弃离生命的。然而,陈巨飞不是,他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热爱生活,即热爱“一截蕹菜、一粒豌豆、一颗花生”,热爱尘埃中每一种微小的事物,这种热爱最终与生活互溶,呈现出最真切的爱的澄澈。于清晨开始,工作的节奏启动,历经少年和青年,陈巨飞已然明晓何为“热爱”的真谛。
难道陈巨飞还没有透彻认识生活的实质吗?不,他认识到了。《空城》一诗中,他写道:“他曾捕捉一只鸟,白头翁/一生的白头也是空的/他的香烟,香烟里的回忆是空的/他住在哪里,哪里就是空城/一城的风雨,是空的。”城市是空的,延伸之意,人世亦是空的,是空虚,而不是空洞。空虚不代表毫无一物,恰恰相反,那是充实的存在。情感因空虚的存在而悸动。在陈巨飞的分行里,我们能感知到他的克制,冷静,压抑,沉稳,巨大的生命之虚无汹涌于生活的前方,无力感、无奈感何其强烈啊。诗歌理论家陈超指出:“它不是一般的虚无,而是类人的广义的巨大的虚无,诗人将这巨大的虚无引入自身,和仅仅表达自身的虚无,是两回事。前者是洞明,后者是哭诉。前者是朗照,后者是昏暗。接下来,我们才可以讨论现代诗另一种‘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形式:与虚无对抗。”从个我狭隘的空虚中走出,进入人类共同的庞大的虚无之境,洞明之,观照之,抗衡之,包容之,这才是一个诗人应行之为。陈巨飞是这样做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陈巨飞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在陈巨飞身上有着一股天生的乐观、坚毅、真诚之品格,这些不单单成就了他的诗歌,也成就了他的生活。
陈巨飞的诗观是:“把湖水磨成时间的镜子,将镜子赠给语言的群山。”陈巨飞一语中的,指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我认为,从陈巨飞的诗观上,已然看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领悟。“我们在陈巨飞的诗里才会读到那么真实的生存图景,读到这些图景中鲜活而令人感动的生命,读到诗人对这些生命深刻而细微的省察,读到陈巨飞与这一切的对话与沟通、接纳与融入,读到诗人审美的观照与诗意的表达,同时,我们读到这样的审美观照与诗意表达中所蕴含的对生命对人间无限的爱意与期盼。”诗评家刘斌对陈巨飞诗歌的总结,把我们洞察的窗页打开,即能清晰地显影陈巨飞在语言与生命双向架构的实践之路。
陈巨飞有一组写父亲的诗歌,我印象颇深。其中有《春天》《父亲》《匡冲》《新坟》等,在这些诗歌中,我深切地读到了陈巨飞内心的真诚。特别是其中的名作《匡冲》,最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你要去匡冲吗?/今晚,你骑着月光即可抵达/山脚下,穷人的屋顶白茫茫一片/你跪在父亲的坟前,像一座漆黑的墓碑/没有悔恨的泪水/也没有骄傲的墓志铭。”真正的悲痛是沉默的,真正的依恋是折返的。“回匡冲吗?!”这句话俨然成为了陈巨飞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是反问,也是设问;是陈述,也是感叹。而这一切,陈巨飞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他在《从母亲开始的写作》一文中写寻母亲的过程,这些写道:“待到家时,我看见一副锁挂在门上,田野还是那么安静。估计母亲是在后山摘茶,于是我站在稻场边,双手围住嘴巴,对着后山使劲喊了一声:妈——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怀疑后山的每棵茶树都听得清清楚楚。几只白鹭也被惊起,它们在山间盘旋,是不是在帮我寻找母亲?整个山谷回荡着我呼唤母亲的声音。”从这一行文中,作为读者,我们似乎能够找到答案。
对于陈巨飞的诗歌风格,我认为他是洗练的,澄明的,智性的。从他对父亲缅怀的诗句中,我们能悟到,他并未把消极、凄悲的情绪带入其中,视野的开阔令他的诗歌域境也变得开阔,写乡村,但不拘于乡村窄小的生活面,“难得的是,他对乡村世界的语言学再造,有一些独特的维度与截面。”(陈先发)在陈巨飞的诗歌中,意象不是单纯的意象,而是情感、智性、景象(事物)的结合,诗句在集中、含蓄、暗示等作用显现的同时,也唤醒了景象(事物)自身的心理能量,这种诗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面对再大的困厄和险境,都必须要迎接,对抗,拥抱,而不能有丝毫侥幸、躲避的心理,更不能希翼有谁来与你共担。与生活的战斗,诗人们没有战友。那是一个人的战场。在《一人书》一诗中,陈巨飞写下这样的诗句:“他记起曾经的国度/缺一位英雄。”也许,在这里“英雄”的所指不是一个形象高耸、战功卓绝的英雄,而是匡冲的一个平凡的朴素的父亲,他是一个农民,他有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儿子。
作者简介:祝宝玉,男,1986年生,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诗选刊》《安徽文学》《骏马》《星星》《作品》《扬子江》《青春》《散文诗》等期刊。
出生于1982年的陈巨飞,至2022年,恰值“不惑”。不惑,不是无惑,它不是指一个人什么都知道了,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清醒认知,对生命的醍醐领悟,对命运的重新评议。值于不惑之年的陈巨飞,用他的诗歌论证了“人生即悲剧”乃是一个伪命题,他还是那么热爱着生活,并在诗歌中予以深情地呼吁。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给人生的定义,亦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人生并非悲剧,而是懊恼,这才是人生中的基本感情。人生之晨是工作,人生之午是评议,人生之夜是祷告。”步入不惑之庚年,往往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总结,继而评价,这一评价并非针对他人与社会,而是针对主体的自我。从陈巨飞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出他在自我跃空后的俯瞰。
在《清晨颂》一诗中,陈巨飞写道:“在蔬菜进城的路上/我遇见一截蕹菜、一粒豌豆/一颗遗落的花生/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空谈”的定义是什么?我理解为那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议论。高蹈入虚幻,而远离真切的尘世,这样的诗人往往是弃离生命的。然而,陈巨飞不是,他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谈”,热爱生活,即热爱“一截蕹菜、一粒豌豆、一颗花生”,热爱尘埃中每一种微小的事物,这种热爱最终与生活互溶,呈现出最真切的爱的澄澈。于清晨开始,工作的节奏启动,历经少年和青年,陈巨飞已然明晓何为“热爱”的真谛。
难道陈巨飞还没有透彻认识生活的实质吗?不,他认识到了。《空城》一诗中,他写道:“他曾捕捉一只鸟,白头翁/一生的白头也是空的/他的香烟,香烟里的回忆是空的/他住在哪里,哪里就是空城/一城的风雨,是空的。”城市是空的,延伸之意,人世亦是空的,是空虚,而不是空洞。空虚不代表毫无一物,恰恰相反,那是充实的存在。情感因空虚的存在而悸动。在陈巨飞的分行里,我们能感知到他的克制,冷静,压抑,沉稳,巨大的生命之虚无汹涌于生活的前方,无力感、无奈感何其强烈啊。诗歌理论家陈超指出:“它不是一般的虚无,而是类人的广义的巨大的虚无,诗人将这巨大的虚无引入自身,和仅仅表达自身的虚无,是两回事。前者是洞明,后者是哭诉。前者是朗照,后者是昏暗。接下来,我们才可以讨论现代诗另一种‘变血为墨迹’的阵痛形式:与虚无对抗。”从个我狭隘的空虚中走出,进入人类共同的庞大的虚无之境,洞明之,观照之,抗衡之,包容之,这才是一个诗人应行之为。陈巨飞是这样做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陈巨飞是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在陈巨飞身上有着一股天生的乐观、坚毅、真诚之品格,这些不单单成就了他的诗歌,也成就了他的生活。
陈巨飞的诗观是:“把湖水磨成时间的镜子,将镜子赠给语言的群山。”陈巨飞一语中的,指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我认为,从陈巨飞的诗观上,已然看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领悟。“我们在陈巨飞的诗里才会读到那么真实的生存图景,读到这些图景中鲜活而令人感动的生命,读到诗人对这些生命深刻而细微的省察,读到陈巨飞与这一切的对话与沟通、接纳与融入,读到诗人审美的观照与诗意的表达,同时,我们读到这样的审美观照与诗意表达中所蕴含的对生命对人间无限的爱意与期盼。”诗评家刘斌对陈巨飞诗歌的总结,把我们洞察的窗页打开,即能清晰地显影陈巨飞在语言与生命双向架构的实践之路。
陈巨飞有一组写父亲的诗歌,我印象颇深。其中有《春天》《父亲》《匡冲》《新坟》等,在这些诗歌中,我深切地读到了陈巨飞内心的真诚。特别是其中的名作《匡冲》,最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你要去匡冲吗?/今晚,你骑着月光即可抵达/山脚下,穷人的屋顶白茫茫一片/你跪在父亲的坟前,像一座漆黑的墓碑/没有悔恨的泪水/也没有骄傲的墓志铭。”真正的悲痛是沉默的,真正的依恋是折返的。“回匡冲吗?!”这句话俨然成为了陈巨飞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是反问,也是设问;是陈述,也是感叹。而这一切,陈巨飞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他在《从母亲开始的写作》一文中写寻母亲的过程,这些写道:“待到家时,我看见一副锁挂在门上,田野还是那么安静。估计母亲是在后山摘茶,于是我站在稻场边,双手围住嘴巴,对着后山使劲喊了一声:妈——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我怀疑后山的每棵茶树都听得清清楚楚。几只白鹭也被惊起,它们在山间盘旋,是不是在帮我寻找母亲?整个山谷回荡着我呼唤母亲的声音。”从这一行文中,作为读者,我们似乎能够找到答案。
对于陈巨飞的诗歌风格,我认为他是洗练的,澄明的,智性的。从他对父亲缅怀的诗句中,我们能悟到,他并未把消极、凄悲的情绪带入其中,视野的开阔令他的诗歌域境也变得开阔,写乡村,但不拘于乡村窄小的生活面,“难得的是,他对乡村世界的语言学再造,有一些独特的维度与截面。”(陈先发)在陈巨飞的诗歌中,意象不是单纯的意象,而是情感、智性、景象(事物)的结合,诗句在集中、含蓄、暗示等作用显现的同时,也唤醒了景象(事物)自身的心理能量,这种诗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面对再大的困厄和险境,都必须要迎接,对抗,拥抱,而不能有丝毫侥幸、躲避的心理,更不能希翼有谁来与你共担。与生活的战斗,诗人们没有战友。那是一个人的战场。在《一人书》一诗中,陈巨飞写下这样的诗句:“他记起曾经的国度/缺一位英雄。”也许,在这里“英雄”的所指不是一个形象高耸、战功卓绝的英雄,而是匡冲的一个平凡的朴素的父亲,他是一个农民,他有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诗歌的儿子。
作者简介:祝宝玉,男,1986年生,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诗选刊》《安徽文学》《骏马》《星星》《作品》《扬子江》《青春》《散文诗》等期刊。